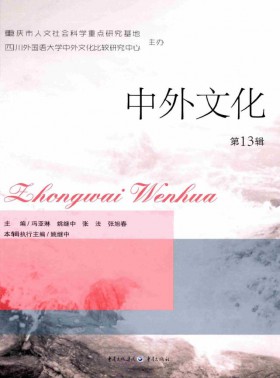[摘要]
一直以来,首都文化研究有两种基本视角,一种是以城市文化视角进行研究;另一种是以城市-乡村共生体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而沿着这两种不同视角,研究者们对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界定以及首都文化未来发展功能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的焦点是首都文化功能未来发展是以高速的城市信息化、现代化为基础,还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为基础。尽管相关文献已经提供丰富的理论源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首都文化以城市-乡村共生体的文化视角并不占主流,但它却打破了以城市文化解释首都文化的单一模式,这为首都文化的深化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关键词]
首都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文化功能
一直以来,提及“首都文化”这一概念,人们头脑中随即浮想出大都市的画面。要对“首都文化”进行解读,也都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产生这种观念的主要原因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近四十年来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变革的“大转型”的现代化建设(波兰尼,2007)。人们在头脑中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认识:提及现代必然想到城市,提及最现代化的城市必然想到首都,而提到首都文化会立即想起大都市文化。而这一认识也成为许多学者阐释什么为“首都文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京津冀一体化以及新型副中心文化建设的背景下,“首都文化”显然打破了首都文化等同于大城市文化的观念认识。因此,本文通过对首都文化研究的视角、概念、内涵、功能以及首都文化功能发展的目的等五个方面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把握首都文化研究的领域与范畴。对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研究者认识和把握首都文化提供切实的理论资源。
一、首都文化研究的两种基本视角
关于首都文化的研究,人们偏好于“城市—现代”的分析框架。只是囿于学者们生活阅历、学科背景和使用习惯不同,对其使用目的会存有一定的差异。学者倾向于把首都文化放置在“城市—现代”的思维框架下进行解读和诠释,是因为人们把首都文化限定在这样一个城市区域框架内,一方面对其形态、流变过程都有较清晰透彻的了解,易于把握;另一方面“城市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自我构建的现代美好形式新型秩序,代表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乔尔•可特金,2006)。而首都内在本质所要求的“首善之区”满足着这种企盼,这就容易使首都被看作是反映现代城市标准的重要力量(雷震宇,2012)。首都是现代的、城市的愿景符合多数人的心理。当然,这种想法仅代表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在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首都文化应该是一个系统文化,既应包含城市文化也应涵盖乡村文化。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第一,首都文化置于“城市—现代”分析框架内,如此分析范式很易让首都文化排除掉传统与乡村文化,最终把首都文化引入到自我发展的矛盾上来。尽管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比,已经超越了后者无论是开放性、多样性、聚散性和扩散性(陈丽旭,2002),但在盖伊•博德(2008)看来以现今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确实是一个缺乏凝聚力与自身自相矛盾的独立王国。它正导致着其内部的文化危机。列斐伏尔(2008)阐释到在以现代城市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下,伴随着城市中已经出现的危机,同样历史悠久的全世界的农业文明也已出现危机。第二,用“城市—现代”的视角作为首都文化研究的框架势必有其局限,这也将直接导致首都文化功能的实践性在今天如何得以发挥陷入到功利与实用性上,以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有偏差的或者成为脱离“人”自身发展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代表传统文化的乡村文化纳入到首都文化中就显现出了很强的必要性。卡洪(2008)认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以机械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已经渗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人们对待城市的文化方式,被单向度的现代工业的理念牢牢地束缚(卡尔•芬格胡特,2007)。人们对于个人自身发展理念已经被现代的工业理念所束缚。正是,在这两种基本视角下,首都文化的概念、内涵、功能在学者之间又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二、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就从“首都”的含义而言,它并非完全指代一座城市。从宏观上讲,首都包含地理范围内的整个行政区域,即含有被管辖的城市也包括其农村。从微观上讲,它仅指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国家政权中枢(彭兴业,2001)。对于“首都文化”,由于首都的宏观与微观的不同界定,以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首都特征,首都文化概念是一个针对不同历史时间、不同国家地域、体制、国情而抽象出来,且反映出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质。所以首都文化也并非一个稳固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通过概念描述的方法,对首都文化进行阐释。刘易斯•芒福德(2008)曾对欧洲巴洛克时期的首都文化进行了如下描述:“法律、秩序、统一”是欧洲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理想,也是当时欧洲各国的首都文化观念,而这一观念又与整个欧洲社会的观念相互作用,突出了首都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塑造。杰弗里•迈耶(1998)也对首都华盛顿做出这样的文化描述:“华盛顿作为一个摒弃神权观念的全新地方,旨在建立民主社会而精心设计的首都,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国玺永存的新秩序。”与此相对的是,他也对晚清帝国首都文化进行了描述:“把北京作为首都的清帝国,却仍以首都作为‘天子’的中心,以神权维持国家的秩序,并以首都的中心地位,把这种文化观念输出到帝国的地方区域。”但不得不说明,直至今日,北京做首都的“神权秩序”观念经过历史变迁与历次运动,其文化内涵已经发生转变,正如贝淡宁(2012)所说:“现在北京这座城市,作为首都文化的内质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政治倾向与政治热情。”显然,对于国外的学者来说,“首都文化”被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其首都文化功能在概念的描述中被体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尽管这些学者没有直接强调首都与城市的对等性,但其观念中已经渗透了“首都相当于城市”的。与外国学者对“首都文化”进行概念描述性相比,国内研究学者一方面把首都文化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作为首都北京的文化界定上来;另一方面,他们却也吸收了国外学者以城市文化看待首都文化的逻辑。因此,在这部分学者眼中认为北京作为首都,首都文化自然强调的是北京的城市性与北京的城市文化。那么在对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解读中,北京的城市文化也就成为主要的对象。孟固(1997)指出,首都北京在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型特大城市。对于北京来讲,它只应该作为一种城市来看待,首都的文化应该反映现代的城市文化(李建平,2013)。沈望舒(2009)在《从首善到人文的心路趋向———浅述构建首都文化特质的着眼点》一文中支持了这种观点,他说“首都文化”彰显的是“首善精神”,而首善精神是首都的城市精神,是北京文化的特质。在此基础上,“首都文化”就成为城市文化,其首都文化的概念被描述为:首都文化源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这一城市地位的客观现实,彰显地域文化与荟萃全国文化的综合优势;它塑造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代表者形象,体现拥抱国家与世界的精神境界;它突出海纳百川的气势和用良田沃土吸容八方建设者的环境条件,表达宽广真诚的心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能构筑起属地民众和机构的凝聚力、归属感(沈望舒,2004)。当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首都文化不完全等同于北京城市文化。执此观念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1)首都文化是一种具有北京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北京除了作为首善之区之外,北京更是作为首都的一种地方性概念。首都文化就是其历史情况、风俗情况、地域情况下所反映出来的地域性特征(萧放,2012)。这里真正地把首都文化置于历史的时间与地域的空间之中。(2)首都文化是以北京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今天北京文化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文化系统,它是全国文化的汇集,又包括本地历史的文化精神。而首都文化是各区域文化展示交流的中心,是各种文化向北京集聚的一种表达。因此,首都文化只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李建平,2013)。(3)北京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地方性文化;另一个为首都文化。首都文化与北京地方性文化二者交叉前行,在不同时代北京文化融入不同统治者所构建的首都文化精神之中,体现不同样式。因此,两种文化是相互交融,且彼此穿插的(阎崇年,2004)。可无论是以城市视角研究首都文化,还是以非城市视角研究首都文化,其“首都文化”的内涵,也是通过物质行为与精神观念两个层次来表达的。从物质行为层面看,郭勉愈(2005)认为大院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为,“建国以后,就社会、政治地位所蕴含的文化能量而言,以干部、知识分子为主体,居住在大院中的新北京人,构成了北京最重要、最活跃的阶层,成为首都城市文化的主角”。彭庆生(2008)认为北京的胡同承袭着首都的文化精神。毕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心、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国各地域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外文化交融的中心,许多文化在胡同中得以体现。当然,地名作为文化的“镜象”(牛汝辰,1993),作为物质世界的象征手段,北京的各大地名与胡同名,也呈现着首都文化海纳百川的姿态。“北京地名中的这部分独具乡土风味的地名,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种意趣(张燕来,2008)。除了大院、胡同等,首都的节日仪式也是首都物质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华民族的首善之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与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最为重要的是,首都的节日仪式与娱乐在现代语境中被转换成政治社会的表达方式,政府行为与民间社会在节日中得以协调,在节日中传达一种政治意识(萧放,2012)。从精神观念层面上看,首都文化的研究较为多样。孔震(2013)认为北京的旗人文化的尚礼、规矩构建了老北京人的价值基础与信仰,是老北京人的文化之根。首都文化正是从这种文化中生发出来的。但这只承认了首都文化的历史渊源。许多学者指出首都文化精神更应该是一种政治的观念反映,更应强调政府的意志。陈荣荣(2005)认为政府在首都文化生活中最关键的作用就是铸造首都之魂。李建盛(2012)认为首都文化是首都精神的映射,其核心为北京精神,即“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王一川,2012)。在此基础上,要具有“政治敏感,民族大局感”“民主法制观念的意识”(王晓燕、刘志方,2009)。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首都文化精神“使人实现现代化”(沈望舒,2007),让首都文化的“文明价值与世界城市对接”(沈望舒,2010);(李建盛,2013)。
三、首都文化功能与文化功能发展
不同学者都对首都文化概念进行了细致描述,首都文化到底是否一定属于城市文化,或者属于地域性文化,再或者是城市-乡村文化的共生体,对于这些并没有共识。但无论从何角度出发,首都文化功能的研究并没以城市文化、地域性文化或城市-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要素为条件,而是以如下三个层面对首都文化功能进行阐释。其一,国家记忆与文化传承。首都文化具有历史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它都保存了建筑、民俗、老字号等文艺形式(郑师渠,2004)。同时,首都文化具有很强的意向,它通过景物相连构成一组国家记忆的符号链条。这种记忆,把景物与文化在心灵上联系在一起,让人们记忆(张法,2004)。其二,联接地方与协调区域。在思考首都文化时,应该注意考察首都文化,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应该把首都文化置于是全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中心点上来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发展研究中心,1996)。并且在一国众多中心城市中,首都城市有着某种意义的最高性和唯一性的地位主导。主导的功能是文化影响和文化辐射的功能。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皆在其中(沈望舒,2007)。首都文化的政治性较强,是整合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政治功能(彭兴业,2002)。其三,行为规范与社会秩序。首都作为首善之区,其文化自身就充满着文化自觉,他让人们理性地看待自身行为,这种自觉功能对于规范社会秩序有着一定的效用(许嘉璐,2004)。相较其他城市,外国留学生评价最高的地区是北京。这一原因则是首都文化的自觉性与市民行为举止在其文化规范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在此氛围中自律、自觉(李春雨,2006)。但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已经不可能逃离空间要素。毕竟“首都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形式,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张宝秀,2012)。那么文化功能应以何种路径进行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是纽约、东京那样打造成为一种信息城市,制造成一种无信息的隔阂,还是如巴黎那样打造一种学术性为底蕴的都市城市(peterhall,2009)。亦或是沿着“田园城市”理论的“人本关怀”逻辑思路,以乡村丰富首都文化,拓展首都的文化功能。从国外的研究上看,关于首都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是沿着两条脉络进行的。一条是,把首都作为城市进行看待,而首都文化就成为城市文化。雅各布森把华盛顿放置于纽约、费城、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共同特征下进行分析,认为城市文化在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吸取着各个方面的先进文化知识,而这些知识被行业精英所率先吸收,并融入到行业文化中,进一步渗透到城市文化内(雅各布森,2006)。另一条是,把首都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联合体进行看待,那么在此之上的首都文化就发展为城市与乡村的联合文化。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即是这种发端,霍华德(2000)指出作为首都伦敦的未来,它应该是由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共同构成,并把自然的风光与城市相结合起来。而“田园城市”只是形式上的设计。在这种观念后,其实霍华德强调的达到“社会城市”的特点,而这种社会城市强调的是“人本”的理念,人利用田园城市达到城与乡、人与人平等的目的,最终构建出这种文化观念。国内对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路径研究,也是沿着西方研究思路的两条主线。一方面,认为首都文化的功能就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继续扩大化。在这种城市背景下,戚本超、周达(2006)指出首都文化承载功能“首都北京的文化职能就是强调北京作为一个历史名城,继承着京都文化”。郭梅(2014)认为北京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因此首都文化的功能除了文化功能外,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李晓江、徐颖(2015)进一步指出“当北京发展成为世界城市之时,首都的文化功能更应该体现在和谐与生态”等理念上。另一方面,关于首都文化以整合乡村文化发挥功能的研究较少,仅有张彦敏(2013)认为:“北京乡村文化建设与北京的区县文化建设应更好的结合起来从而面对今天我国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可以发现,对于首都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整合的研究,在今天社会下,成果并不丰富,这给我们留下了充足的研究空间。我们还可看到,今天乡村蕴含着丰富巨大的文化宝藏,乡村文化已经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失去的乡土认同和文化自信(高小康,2010)。毕竟城市本身就是“把人类与巨大的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手段,是一个促使宇宙,世界安定与人和谐的方式”(凯文•林奇,2011)。
四、研究评述与思考
以上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基于历史或是现实、国外或是国内的视角来探讨首都文化的概念、内涵、功能与发展路径,都为首都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但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与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我国来讲“首都文化”到底是地域文化、还是北京城市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尽管从文献综述上可以发现一部分研究已经做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多视角考察首都文化问题。但归根结底,国内学者们还是把我国的首都文化作为北京的城市文化进行研究。然而,这就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前学界把首都文化的研究陷入城市文化研究上来,不仅忽略首都传统文化内容,也忽视了首都乡村文化内容,这造成呈现出的首都文化的功能研究缺少全面性与整体性。导致以“城市-乡村”相结合的文化视角研究首都文化并没有得到共识。而之所以缺少这种共识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许多学者眼中,“城市—乡村”框架自身的矛盾性。而这里涉及两对概念即“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是否矛盾、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学者在建构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关系的同时,指明了城市与乡村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传统与现代文化导致的。滕尼斯(2000)指出:“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共同体’文化形态,共同体是‘传统’的它相当于农村。‘城市社会’文化形态是现代文化形态。都市社会是崭新的现代的,它相当于大都市。”衣俊卿(2005)针对我国也指出:“中国以农业作为传统,农业追求的是天的状态。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因此,在中国人视野中,习惯于对整体的知觉把握和经验认识,没有培养起来对事物内在结构的理性分析与把握,尤其对于乡村农民来说,由于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乡村,乡村文化影响正是受传统农业文化的延续。因此必须借助工业文明建立起技术理性、科学思维、分析精神和主体意识、参与精神。让城市以工业文明下的理性化与科学精神,改变他们的思想与文化状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如此二元结构似乎很合理。可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真是二元悖反的吗?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道德、民俗、信仰产生于乡土之中(冯友兰,2012)。乡村对于中国,犹言城市对于西方,因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城市,其道德、信仰由城市而塑造(温铁军,2015)。谁忽视了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就很难理解各自的内在含义(刘钊,2012)。为了说明此点,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就明确说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两种文化体系发生着冲撞,但不能割裂来看问题”。尽管中国的文化正脱离原有的农业文化环境向工业文化转换,而农业文化的观念基础是“知足”精神,工业文化的观念基础是“无厌求得”,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价值体系。反映在经济上,就是乡村经济的自给自足,与城市经济的“大工业”生产对乡村的剥削。城乡之间应该是有机循环的,从而在经济上解决“黎民不饥不寒的状态”,在文化上走向相互融合。毕竟如施坚雅(2007)曾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城市样态那样,“中国城市的宇宙论是由取自‘大传统’核心思想的要素构成,并借于农村的小传统所丰富。”城与乡一直存在着联系。朱媛媛、曾菊新(2013)更是以武汉为例,认为城乡文化在空间上是可以整合的,并用定量的方式,证明着城乡文化融合的程度。显然,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尽管充斥着矛盾,但也充满着融合的可能,它们存在着互相依靠的基础(肖小霞、德频,2003)。那么,在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为表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关系?纵观历史,传统与现代可以说是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基础上有序地形成,完全脱离旧秩序而产生的新秩序更是不会长久。因此,现代之前必定有一个传统作为基础,现代化之后又为未来形成新的传统。毕竟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做的功能适应(何星亮,2003)。而对于传统来讲,传统又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永远向未来打开无穷的可能性,因而传统首先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而不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许明,2010)。正如郑杭生(2008)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现代人所说的传统是为现代而生的,因为唯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只有通过现代,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唯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应对时,它才能被我们思考与把握。既然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那么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来讲,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矛盾。因为,现代性脱离不了各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金耀基、周宪,2003)。“不同文化需求,满足人们不同部分。传统的文化价值固然属于价值理性,可以说是根植于人性的内在要求;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虽然不少,是属于工具理性范畴的,但科技与物质生活素质的改善又何尝不是根植于人性的需求”(陈来,2009)。在以现代文化为主导的今天,传统文化在扮演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先人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以此作为新的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贝尔,2012)。最为关键的是,正如陈来在二者文化融合中所强调的那样“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以决裂传统为途径,其关键可能在配置合理的文化元素和获得一个良性的结构,使多元文化系统的合成指向较为理想的方向,而不是强求系统中每一个元素都指向同一方向”(陈来,2009)。在这里对“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强调,并非要对这两组概念进行详细说明,而是要对首都文化研究框架的逻辑前提进行强调,指明对未来首都文化研究的方向。一直以来,关于首都文化的研究已经陷入了城市研究与现展研究之中,城市与现代已然成为首都文化研究的主流视角。但事实上,对于首都文化的研究应该“兼顾城与乡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不能一味地崇尚“城市”“现代”,也不能一味的地奉“传统”“乡村”为圭臬,而是理清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整体、全面地把握“首都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当然,关于城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解释与梳理,也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新的首都文化结构缔造了基础。在这个结构中,“乡村文化”的价值地位和其他文化元素相互作用,使得整个首都文化系统不再表现为过渡的现代化和泛城市化特征,而更多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对未来的展望。
作者:任超 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研中心
[参考文献]
[1]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雷震宇.“北京精神”对首都城市文化发展的意义及路径探析[J].北方文学,2012(4).
[4]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5]盖伊•博德.完美的分离[C]//汪民安、陈永国,等.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列斐伏尔.城市化的权力[C]//汪民安、陈永国,等.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M].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
[8]卡尔•芬格胡特.向中国学习———城市之道[M].张路峰,包志禹,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9]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叠加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1).
[10]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1]杰弗里•迈耶.鹰与龙———华盛顿与北京比较[C]//城市社会的变迁.王旭,黄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贝淡宁,艾维纳.城市的精神[M].吴万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13]孟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首都文化[J].北京社会科学,1997(3).
[14]李建平.北京文化的特点———兼论北京学与北京文化[J].北京联合大学,2013(1).
[15]沈望舒.首都文化与首都文化建设[J].北京社会科学,2004(3).
[16]萧放.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2).
[17]李建平.传统节日与北京文化[J].新视野,2008(4).[18]阎崇年.北京文化的历史特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5).
[19]郭勉愈.北京性地方传统:大院与北京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4).
[20]彭庆生.突出北京特色拓展胡同文化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08(6).
[21]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22]张燕来.北京地名和地域文化[J].北京社会科学,2006(4).
[23]萧放.北京端午礼俗与城市节日特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1).
[24]孔震.北京旗人文化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25]陈荣荣.从“798”引发的思考看政府在首都文化生活中的作用[J].首都经济贸易学报,2005(6).
[26]李建盛.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1).
[27]王一川.谈谈“北京精神”中的“厚德”[J].北京社会科学,2012(1).
[28]王燕晓,刘志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首都意识”研究[J].求实,2009(1).
[29]沈望舒.人的现代化与首都城市文化的首善精神[J].城市问题,2007(4).
[30]沈望舒.首都“文明价值”:北京之“世界城市”路径[C]//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2010年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
[31]李建盛.北京文化发展报告———北京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文化中心城市:任重而道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2]郑师渠.“首善”之区与北京文化建设[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5).
[33]张法.什刹海与北京文化记忆[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3).
[34]北京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首都文化现状考察与建议[J]北京社会科学,1996.
[35]沈望舒.中国首都学与首都文化研究建设[J].北京学研究文集,2007.
[36]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版,2000.
[37]许嘉璐.首善之区需要首善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4(3).
[38]李春雨.北京文化的异域审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39]PeterHall.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童明,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40]简•雅各布森.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41]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2]戚本超,周达.北京城市职能发展演变[J].城市问题,2006(7).
[43]郭梅,吕拉昌,等.北京文化资源的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4(4).
[44]李晓江,徐颖.首都功能的历史、现状及完善[J].北京人大,2015(8).
[45]张彦敏.世界城市视域下的北京乡村文化发展研究[C]//郑文堂,华玉武.世界城市战略定位下谈北京乡村文化建设.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46]高小康.内卷化:乡土文化复兴之路[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
[47]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8]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9]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赵复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1]温铁军.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的复兴[EB/OL].中国乡村发现.
[52]刘钊.城市化视域中的乡土文明:冲突与整合[J].前沿,2015(1).
[53]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54]朱媛媛,曾菊新,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与优化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3(10).
[55]肖小霞,德频.冲突与融合: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J].学术论坛,2003(3).
[56]何星亮.对传统与现代及其相互间关系的阐释[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57]许明.本土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孕育生长———反思近三年的传统文化之争[J].社会科学,2010(1).
[58]郑杭生.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发明[J].天津社会科学,2008(3).
[59]金耀基,周宪.全球化与现代化[J].社会学研究,2003(6).
[60]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
[6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上海:凤凰出版集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