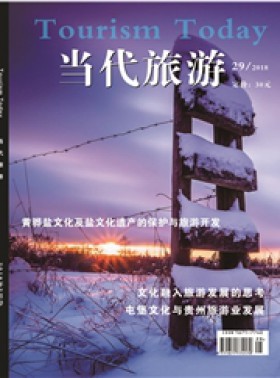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文化旅游受到旅游开发者的青睐。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互动的整体性评价、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传承中各要素的影响研究、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模式与机制研究、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传承的策略研究等四个方面,对相关问题的学术前史进行了述评。
关键词:旅游;文化传承;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旅游在国内逐渐兴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更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地区选择通过自身所蕴藏的丰厚的文化资源吸引游客,走以文化旅游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文化传承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对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进行专门、系统地研究十分必要。1993年,李慕寒[1]最早提出“民俗旅游具备传承性的特点”,随后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旅游背景中的文化传承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
一、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互动
肖曾艳[2]阐释了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有两种互为先导和目的的互动行为,建构合理的互动体系能促使二者进行良性互动。范晓峰[3]认为:要以民族文化传承作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前提,以发展文化旅游业作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许多学者就旅游开发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通过不同视角就不同个案做了研究,对旅游开发与文化传承互动进行了整体性评价,认为:旅游开发对文化传承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但旅游开发对文化传承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的影响。王三北,高亚芳[4]从价值理性回归的视角阐述了旅游活动使文化传承从颓败到重拾,再到在传统文化价值理性支配下进行传统文化自觉挖掘与传承的升级演进。刘社军、吴必虎[5]将文化与基因类比,认为通过旅游开发可将无形遗产有形化、大众化,优化文化基因赖以生存的遗传基质,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双赢。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传承场和传承内容的影响。廖冬梅、张诗亚[6]认为:旅游开发改变了丽江文化传承的载体——古城,也扭曲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从而阻碍了文化对下一代的传承。肖佑兴[7]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旅游流系统、旅游地文化系统、旅游制度系统三者的互动影响了旅游地文化传承,并将旅游对文化传承的消极影响归结于旅游流系统的驱动作用与旅游地文化系统的响应行为二者的辐合效应和旅游地文化系统不协调。事实上,旅游开发有助于培育传统民族文化的现代生存空间,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保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民族文化的传承“自然而然”地也就出现了,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利弊并存中利大于弊。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传统节日和仪式由于其在旅游中独特的魅力而被学者们关注。饶峻姝[9]认为:开发节庆旅游使人们通过节日仪式的展演与传说的讲述,直接与祖先对话,反复重温、体味传统,在耳濡目染中自觉理解、接受传统,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交融和发展。庞玮、马耀峰[10]认为:宗教旅游蓬勃发展,使得传统宗教文化通过异域与本土、传统与构建的传统、文化与市场、记忆与再现四个层面进行文化传承与构建。同时,赵世林[11]等学者注意到:民族传统节日是一种脆弱而极具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开发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犹不及。吴波、田维民[12]认为:由于在基本目标、价值取向上存在矛盾和冲突,旅游开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对传统节日之保护与传承造成消极影响。针对文化传承对旅游开发的影响这个问题,笔者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或有纰漏,没有发现专门对其进行阐述的研究,而“顺带提及”的文章颇多,这些研究基本达成了文化传承使文化得以延续,而文化是文化旅游开发的资源,保证文化传承可以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文化传承对旅游开发的影响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话题,例如,文化传承助力旅游开发的机制;文化传承与开发体验旅游等,这些问题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中,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二、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
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并未止步于宏观评价,许多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笔者认为,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应该具备一定的范式,从而使得研究更为系统和科学。段超[13]认为:文化传承体系是多种元素、多环节组成的复杂系统,传承体系各要素、各环节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多重关系,这些要素包括传承主体(传者与受者)、传承场、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和保障体系。笔者通过这五个要素,将学者们对旅游开发影响民族文化传承的细化研究分为五个方面。
(一)传承主体
旅游能为文化传承培养群众基础[14]。旅游开发对传承主体的影响既体现在旅游改变传承主体的境遇与行为,又体现在旅游活动通过对传承主体文化认同的影响,进而影响民族文化传承。这两个方面中,传承主体的认同研究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话题。杨杰宏[15]认为:在旅游情景下,东巴“祭司进程”使传统和民间祭司扮演了“城市牧师”、“民间心理医生”等角色,丰富了传承主体的身份,为传统文化传承创造新途径。韩璐[16]认为:传承主体将实践活动搬上“象征性舞台”以实践表演与传承任务,根据游客的在场与缺场,对民族文化符号与意义进行包括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台前幕后的空间重叠等形式的重构。梁丽霞、李伟峰[17]关注旅游开发中的女性传承主体,认为:在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旅游地女性东道主成为民俗传承的主体,她们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对女性东道主自身以及旅游地的民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旅游激活了传统文化,唤醒了民族自觉[18]。郭山[19]认为:旅游通过对共同体认知和价值观的直接干预,影响了共同体成员对有用性的评判,从而间接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杨慧[20]认为: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得以不断展现,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白杨[21]认为:发展民族旅游,将会实现族群认同的文化要素与民族旅游开发项目的完全对接,使旅游成为一种文化事业。在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研究的方法上,孙九霞[22]提出: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应该考虑到旅游地族群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并认为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其族群认同也会被旅游活动所强化。
(二)传承场
阚如良、李肇荣[23]提出:在旅游开发中保护文化生态,提倡社区旅游。光映炯、张晓萍[24]认为:旅游开发中“传统”的传承场具有了现代“旅游场域”的新的传承特点,反映了在社会经济大发展时代下的特有传承环境。邓小艳[25]基于文化传承源在社区,而且承载社区的特点,选择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践行方式,有利于保护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高春利[26]认为:在旅游开发中,保护文化空间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文化空间保护的根本,是对能够保持当地文化特征的群体的保护。传承场可以分为“自然场”和“社会场”。旅游区通常表现为自然场和社会场综合的传承场形态。对于旅游开发背景下传承场的研究是有所不足的,主要体现在并没有学者就旅游开发是如何通过对传统传承场的改造或构建新的传承场来影响文化传承的,许多研究对这个问题都有所提及,但没有形成有建设性的观点。
(三)传承内容
在旅游开发对传承内容的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旅游如何影响文化的原真性,如何在确保文化在旅游开发中保持原真性,从而使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容规避异质化。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纪念品原真性及舞台表演的原真性两个方面。张瑛、高云[27]认为:商业开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受到扭曲,从而使文化失真。吴兴帜、罗沁仪[28]主张:在旅游开发中手工艺遗产保护传承以手工艺品的原生性主体对其分类为指导,以“手、工、艺、品”四个层面为方法,从而实现手工艺遗产的活态、原真性保护传承。刘燕英[29]提取了赣南文化的文化基因并在传承赣南地域文化基础上将文化基因注入旅游纪念品设计,认为:此举有利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和文化传承的延续。孙海洋[30]认为:应该进行区域特色文化、现代多元文化与旅游纪念品相结合的产品设计,强调民族特色元素的旅游纪念品的造型、色彩、材质及功能,让民族文化在时尚中传承。在舞台表演文化的原真性上,徐赣丽[31]认为:在旅游开发中,展现出的文化内容会通过“迎合游客”而与原本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差异,但基于“后台”的隐蔽性,当地人的舞台表演对其日常生活的传承影响是有限的。其实,只要能够正确处理“前台”和“后台”的关系,则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为当地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会增强当地人的文化自豪感,增强人们传承本土文化的信心和使命感[32]。在这个方面,杨振之[33]根据外国学者马康纳的“前台”与“后台”理论,提出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前台—帷幕—后台”模式,对于文化原真性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HansSteinmuller[34]认为:文化持续性和真实性在于实践中的正确传承,而非物质材料本身的真实来源,探讨中国旅游活动的真实性问题,重要的是要关注文化传统的正确规范的传承及适宜恰当的旅游体验方式。但由于国内外对于文化原真性的讨论在旅游背景下的文化研究领域经久不衰,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不再进行赘述。应该看到的是,加深对文化原真性的探讨,有利于深入理解旅游开发对文化传承内容的影响。
(四)传承方式
旅游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35]。光映炯、张晓萍[24]认为:在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市场对民族文化的重复利用开发与商业化制造扩大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是一种“旅游化”的传承方式。马振[36]认为:旅游影响了“西兰卡普”文化传承的各个要素,提出“旅游生产性传承”的概念,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生产性传承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全部或主要要素与旅游要素相重合。许多学者也在探索多种传承方式综合的途径。施伟萍[37]主张在职业学校设立“非遗传承教学基地”,学校与企业深度合作,非遗大师进校参与教学,开展对学生以技能培养为主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在传承方式的探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对“旅游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这个观点进行建构。此外,在旅游开发中,如何利用多种文化传承方式相结合来进行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
(五)保障体系
由于我国大众旅游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的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为旅游开发中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例如,2005年《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强调: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使之在“原生”环境中得以传承与发展。2006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规定:传承人及传承单位有偿提供其掌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以赋予传承主体知识产权。2009年,海南省通过《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村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建设代表性项目“传承村”。这些制度体现了保障体系与其他传承要素的互动。学者们也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雷蓉、胡北明[38]认为:旅游开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胡小东[39]认为:在政府对西江苗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的确进行了有意识的保护,但同时也因为对当地文化传承的忽视而使当地的传统文化的确受到了“无意识”的冷落。李欣华、吴建国[40]认为:旅游开发中,国家法规、寨规(习惯法)和“工分制”的综合作用使村寨文化得到有效地保护和继承。翁时秀[41]认为:旅游开发中所有文化传承保护所采取的措施都需要符合“合法性”,且同时具备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即文化传承者既认可文化的价值,又遵守保护政策和行为倡议。
三、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模式与机制
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对于文化传承模式与机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能籍此实现开发合理化的实践途径;另一方面,通过对模式与机制的研究,也为旅游开发中文化传承的研究提供视角和方式。晏鲤波[42]探索了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试探性地构建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王德刚、田芸[43]认为:“旅游化生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时代性、经济性、先进性等特点,是非遗传承的一种重要模式。肖佑兴、李悦、何向、胡丽芳[44]认为:旅游地文化传承模式有家庭传模式、社区传承模式(包括社区+旅游就业的文化传承模式)、学校传承模式、市场传承模式(包括旅游商品生产型,旅游表演型)、社会传承模式等五类。罗茜[45]认为:应在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中保护与开发、继承与发展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由政府、旅游企业、当地村民和学者等四方力量搭建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主体合作模式。吴亚平、姜似海、陈志永[46]构建了旅游发展语境下侗族大歌保护与传承的动力机制模型,主要由包括当地人自身动机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包括政府、企业、游客和学者参与的外在动力机制构成。李晟[47]通过分析文化传承的内在积极、消极激励因子,外在积极、消极激励因子四类因素,建构了旅游背景下“非遗”传承激励机制。刘丽[48]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构建了古镇旅游开发与文化传承发展共生模式及运行机制。王冬敏[49]认为:生态博物馆传承模式是采取“生态保护,活态传承”的一种公司加村寨的旅游模式,传承主体间互动少,多为“表演一欣赏”的关系,在有效传承这一文化遗产上作用还非常有限。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将模式和机制并而论之,但二者其实是有明显区别的。模式是指“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机制在“社会学中的内涵可以表述为‘在正视事物各个部分的存在的前提下,协调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因此,在模式的探索上,应该更加关注传承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而在机制的探索上,既要关注传承过程中各要素的作用运行方式,还要关注包括政府、企业、学者等实际参与到文化传承中的各个部分作用运行方式。在规范的清晰界定之后,还应该在模式的现状研究中实事求是,在构建机制和模式时因地制宜地符合当地文化传承或旅游背景下文化传承的实际情况,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四、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传承的对策与策略
学者们为旅游开发中的文化传承制定策略,一方面是为减少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消极影响提供对策,另一方面是就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如何互促共赢的问题展开探讨。学者们制定的策略体现出实践性策略和理念策略两个层面。就可操作的实践性策略而言,阮洛瑶[50]提出:要在旅游开发中重视保护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提倡传承与开发过程中应重视以人为本。龙先琼、蒋小梅[51]认为,在旅游开发中需要坚持整体性原则,既注重文化内容的整体性传承,又注重文化在民族心理和精神上的认同作用,培养“本土文化传人”,同时还要注意保护文化传承的环境。阳国亮、邓莹[52]基于“原真性保护”原则,认为:应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活动的质量评估,应加强对传统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转型指导。唐嘉耀、辛建荣[53]认为:传承与创新要始终贯穿于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全过程,要对内容有所选择,以解决好庸俗化、缺乏个性和粗糙仿制的问题。林娜、张博文[54]认为:应将文化传承人培养引入旅游教育,整合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资源,推进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本土化,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顾金孚[55]提出建立法律、行政和经济相结合的保障机制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王德刚、史云[56]认为:“社区自主”与“有限干预”是以社区利益为主导的应答途径,前者是根本性原则,后者是积极手段。徐赣丽[57]认为:应重视学者在旅游开发与文化互动的作用,建立合理的保护框架。刘小燕[58]认为:建立完善的旅游保障机制,保证其传承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首先要有国家遗产保护政策的支持;其次,要有资金投入来组织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再次,要有遗产传承活动的场所;最后,要有组织遗产传承活动的专业队伍。由于政府与企业在旅游地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扮演了保护者和开发者的身份,他们的开发理念值得重视。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应该先于旅游开发开展起来[59]。吴波、田维民[12]认为:面临着不断被弱化乃至消亡的传统节日,应该利用旅游开发来将他们传承和发展下去,但发展旅游业只能是传统节日得以保护和传承的一种手段,处于服从和服务之地位。薛群慧[60]认为:旅游开发中,活态文化的存在价值是核心,经济价值是派生的,存在价值决定了经济价值,所以要从传承活态文化出发进行旅游开发。陶玉霞[61]认为:应遵循“小众旅游”、区域规划、文化发展、消费引导等设计原则,构建乡村游憩发展中文化传承功能的实现途径。不难看出,很少有学者提出关于如何提升传承主体在旅游开发背景下适应现代化的策略,而普遍偏重旅游的管理者与开发者的角度。诚然,传承主体在旅游开发和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属于弱势群体,而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也很难使策略真正适用于传承主体。但是通过对传承主体适应策略的研究,有助于塑造典型和榜样,使旅游开发背景下进行文化保护与传承成为各方面共同努力的事业。
作者:马路遥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