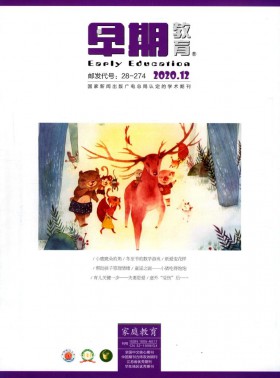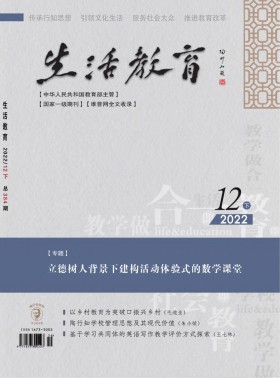【摘要】
迄今为止,人们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仍然深受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影响,其典型表现就是将通识教育简化为知识教育,使通识教育本身面临多方面的危机。文化哲学则主张将通识教育从知识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通识教育具有鲜明的文化品性,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文化陶冶而非简单的知识学习;通识课程的设计重在恢复和重建课程知识的文化脉络;通识教育的教学实践则应该着力体现诠释、对话和理解,使知识蕴含的意义世界不断向学习者敞亮。
【关键词】
通识教育;文化哲学;文化陶冶
一、文化缺失与大学通识教育的危机
破解专业教育、知识教育的褊狭,促进学生心灵与人性的觉醒,这一直是通识教育的根本旨趣。但是,在实践中,通识教育似乎并未超越知识教育的逻辑,也未能实现“人性教育”的美好理想,其突出表现是通识教育被错误理解为“简化版”的专业知识教育,背离了通识的精神与要义。通识教育实践困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根源,即近代知识论哲学对人类思维的深刻影响。知识论哲学强调主知主义,知识的获得成为哲学思考的焦点,知识教育也成为教育实践的中心。知识论哲学把通识教育简化为知识教育,忽视和遮蔽了通识教育原本具有的文化向度。而通识教育文化向度的缺失,又使通识教育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重大危机。第一,通识教育课程性质的迷失。陈向明教授认为,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应该成为专业教育的“灵魂”和“统帅”[1]。但是,知识论哲学却狭窄地从知识的立场来理解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由于既有的专业教育强调知识的深度,通识教育似乎就只能强调知识的广度,这就导致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肤浅化,甚至娱乐化、媚俗化,通识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专业教育的灵魂,反而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就指出,有些通识课程投学生之所好,“例如教师只教通俗武侠小说,却置李白、杜甫、《红楼梦》于不顾。于是,学生喜好《哈利波特》,却不读莎士比亚。”[2]通识课程娱乐化的背后,正反映出教育界对通识教育课程性质认识的模糊。第二,通识教育课程目标的错位。在知识论哲学的视野中,通识教育的目标往往被错误的理解为培养“通才”型的“知识人”。然而,在知识不断分化的大背景下,试图通过有限的课程学时来培养“通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严重的是,“知识人”的目标定位使通识教育深陷在学科主义、专业主义的逻辑之中,远离了其培养“完人”的终极旨趣。对此,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曾指出,通识课程不是为训练未来的专家设计的,现有的通识课程没有脱离专业教育的轨道,往往在无形中强化专业意识,结果不仅使理科的学生学习文学感到无趣和沮丧,也使文科的学生学习科学而感到畏惧[3]。第三,通识教育课程价值的异化。通识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化陶冶与文化传承。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指出,通识教育的“主导思想”应该是文化,通识课程的设计应该揭示:“文化的丝线是以什么方式被编织到教育的织物里面的”[4]。但是,知识论哲学倡导实体性思维,关注的是那些可以言说、可以传递的显性知识,忽视知识背后所蕴含的人文脉络与精神力量。在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影响之下,通识教育容易蜕变为简单的知识教育,忽视学生健全人格与精神境界的培育,丧失了大学教育应有的文化之根。
二、知识观的转变与通识教育的文化意蕴
通识教育要实现人性教育的理想追求,就必须超越知识论哲学的窠臼,从狭隘的知识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并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与建构。在文化哲学看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显著差异在于对待知识的不同态度。文化哲学认为,知识不仅具有逻辑的属性,更具有文化的属性。知识论哲学的缺陷在于剥离知识的文化脉络,片面强化知识的学科逻辑,结果使知识变成冰冷的概念与命题,遮蔽了知识背后所蕴含的人类精神力量。对此,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做了深刻论述。他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区分了两种对待知识的方式:一种是“事物的感知”,即将知识看做外在于人的“物”,看做要占有的对象;另一种是“表达的感知”,即将知识看做人的文化实践,并重在诠释知识背后的精神力量。在第一种情况下,学习者所面对的不过是“事物的世界”,在第二种情况下,学习者所面对则是“人格的世界”[5]。遗憾的是,专业教育往往以技术性思维的方式将知识简化为“事物”,正如卡西尔指出的,“这个事物的世界根本就没有灵魂”,生命的体验在这种技术性的知识传授中是被压抑、排斥甚至消解的,“结果是,人类文化难以在这种自然图景中找到它自己的容身之地。”[6]从文化哲学的知识观出发,通识教育迫切需要恢复和重建其原本具有的文化向度,并主动彰显自身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追求。通识教育的目的也不是简单的知识占有,而是文化的陶冶。据此出发,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品性应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通识教育与人文底蕴。知识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符号,而是凝固着人类巨大的精神力量,体现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无止境的追求。卡西尔就反复强调,我们不能把知识“看作我们在学校所学的那种枯燥乏味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是对活生生的思维和表达形式的探究”[7]。以科学为例,科学不仅仅表现为静态的科学知识,更是蕴含着科学精神、科学伦理乃至科学世界观。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就指出,科学知识暗含着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他将这种精神气质概括为普遍主义、共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8]。通识教育视野中的科学教育应该着力引导学生体悟科学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同样,在通识教育中,文学也不能被简化为文学理论知识,而是应该着力体现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学家的境界与追求。总之,种种知识与文化的形式,其背后都蕴含着人类的精神力量。因此,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不是占有知识,而是精神陶冶。雅斯贝尔斯对精神陶冶的价值做了深刻论述。他指出,占有知识不等于精神陶冶,占有知识只不过是习得精神内容的代名词,对人而言也只是一种外在的财富。但是,精神陶冶则重在改变人,帮助人成为他自己。“决定教育成功的因素,不在于语言的天才、数学的头脑或者实用的本领,而在于具备精神受震撼的内在准备。”[9]通识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学习者“拥有一个精神世界”。
2.通识教育与思想启蒙。知识作为人类的文化成果,同样也彰显着人类思想的进程,即知识背后蕴含着人类对宇宙及人生根本问题的困惑、思考与求索。知识作为“事实”可能会不断更新,但是知识背后的思想却可以跨越时代的阻隔,而且还贯穿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可以说,知识的思想性才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知识得以融通的核心纽带。正如阿德勒对名著研读课程所做的辩护:名著虽然成书于遥远的古代,但是名著中提出的问题却具有时代的穿透力。“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通常都是人们在思想和行动领域面临的一些老问题”,因此对于理解和面对当前的问题,名著仍然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力[10]。通识教育不是简化版的知识教育,而是肩负着思想启蒙的重要使命。通识教育应该敞亮知识背后的思想力量,凸显知识蕴含的问题意识,揭示知识背后人类的卓越思考,引导学生主动地与人类思想“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学生“求通”的眼光与见识。唯有求通,才能目光远大、融通识见,这也正是通识教育的真正魅力之所在。对此,倡导通识教育的思想家们都有精辟的论述。例如,纽曼就指出:“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或理智”[11]。列奥•施特劳斯则认为:“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的心智与卓越,……在于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交谈”[12]。思想启蒙意味着打破专业教育的学科边界,以求通的意识去发现知识之间潜在的思想脉络。赫钦斯指出,专业主义导致的大学缺陷就是“无序”“大杂烩”“孤立主义”,“现代大学好似一本百科全书”“它拥有从艺术到动物学的各类系科;但是学生和教授都不知道系科间真理究竟有什么关系,或可能是什么关系。”专业教育以碎片化的知识钳制了学生的思考,结果反而导致了“反理智主义”[13]。与此相反,通识教育应该到思想深处去发现知识之间或隐或显的联系,以“求通”的见识来追求万有相通、古今融通[14],从而提升学生的洞察力与思考力。
3.通识教育与时代精神。在文化哲学看来,知识作为人类的文化产品,必然凝固着时代精神的烙印,也即是说,知识背后蕴含着时代的崭新课题,体现着时代的价值观念,折射着时代的潮流与走向。陈寅恪先生关于学术研究之“预流”的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意义。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5]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把握时代精神与时代潮流,才是学术研究的“通义”与真谛。同样,人类不同的知识领域,都可以看成是对特定时代精神的能动性回应,因而都反映着时代的精神与潮流。例如,梅尔茨在论述19世纪欧洲思想史时指出,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科学思想就是19世纪的时代精神,科学思想渗透在19世纪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16]。文化哲学对时代精神的重视,意味着通识教育应该引导学习者透过知识的学习去理解人类文明的总体历程,把握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背后的时代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地形成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可以说,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乃在于进入时代的潮流、把握时代的精神,使通识教育真正成为追求“智慧与至善”的教育[17]。
三、通识课程设计的文化自觉
为彰显通识教育的文化品性,通识课程的设计应该超越知识中心课程的设计模式,重在恢复和重建课程知识的文化脉络,使通识课程能够更好地实现文化陶冶与人性教育的理想追求。
1.课程统整要凸显文化实践。知识论哲学及其对学科专业化的强化,使通识课程丧失了统整的中心,这是因为通识课程所涉及的知识是多元、异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型之间根本找不到实体性的统一和联系。通识课程在实践中出现的随意化、碎片化倾向正是这种理论缺陷的具体反映。在文化哲学看来,通识课程统整的中心不是学科与知识的逻辑,而是人类的文化实践与文化追求。通识课程应该回归生活实践,关注人类文化实践中的问题,体现人类文化追求的方向。以历史学为例,历史学不是抽象的知识考古,而是对人类文化生活的深刻洞察。“历史学家并不只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史次序排列的事件。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着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18]以文化实践为中心,意味着通识教育的课程形态不应该是封闭的学科课程,而应该是开放式的、主题式的、问题导向式的,并且以关联课程、广域课程、融合课程、核心课程等形态出现,使通识教育更好地切近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重大课题与时代潮流。
2.课程内容要拓展文化背景。通识课程关注的不是知识的工具价值或实用价值,而是知识所蕴含的文化陶冶价值,即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独特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等对学生成长的重要影响。因此,通识课程的内容不是狭隘的知识体系,而是应该囊括多元、复杂而广泛的文化背景,这也是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显著区别。例如,科学类通识课程不应该像专业教育那样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逻辑体系,而应该更重视科学的历史、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家的个性特点等文化背景因素。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也对两种不同的科学教育进行了对比分析:专业教育视野下的科学教育强调的仅仅是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忽视对科学之文化背景的批判性考察,“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的力量有其局限性,即它通常并不提供对总体关系的理解”;通识教育则相反,“通识教育中的科学教学应该宽泛而完整,它包括科学思维模式与其他思维模式的比较、各科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比较与对比、科学与它本身的历史以及与人类通史的关系、科学与人类社会问题的关系。”哈佛委员会认为,“对一般学生来说,只有这种更宽广的视野才能赋予科学的信息和经验以意义和永久的价值”[19]。
3.课程组织要聚焦文化演进。历史是人类文化得以展现的重要中介,只有在历史中我们才能看到人类精神演进的历程,才能领悟文化蕴含的生命意义。因此,文化哲学尤其重视历史意识,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时态的分析。“文化现象更为明显的受到生成的制约,它们无论何时都不可能游离于过程的溪流。如果我们离开语言发展史、艺术史和宗教史,就不可能从事语言学、艺术科学和宗教科学的研究。”[20]通识课程的设计要树立历史的意识,必须从观念到实践发生重大的转变。首先,通识课程的编制要超越以泰勒为代表的传统课程开发模式。泰勒模式的核心是以逻辑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知识被按照纯粹逻辑的方式进行组织,知识发展的历史脉络被强行阉割,这种知识教育看不到人类精神的创造历程,因而难以发挥文化陶冶的教育作用。其次,通识课程的脉络要重视思想史。思想史隐藏在知识背后,是人类精神生命之创造能力的具体展现。但是,思想史不同于编年史,仅仅将知识或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不能反映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正如卡西尔所言,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是理解人类的生命力,然而编年史只不过是一大堆历史事实的堆积,我们从这些事实和材料中不可能看出历史真正的生命力[21]。通识教育要重视思想史,就必须尽可能挖掘各种学科知识背后所隐藏的人类思想活动的历程,并且以思想史为主线来组织课程内容。
四、通识教学实践的文化追求
1.培育文化的意识。承担通识教育的教师需要有敏锐的文化意识,能够将知识理解为文化现象,自觉地从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和理解通识课程的内容,认真去挖掘和梳理知识背后的文化脉络。事实上,文化意识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时代潮流,通识教育完全可以从这些学术资源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以数学为例,数学背后的文化意蕴已经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美国数学教育家克莱因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一书中就指出,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力量,数学思想持续深入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同样,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历史,他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同文明的演进过程与相互接触,并且指出伟大的文明往往源于艰苦环境的刺激,并且都彰显了人类的巨大努力,文明的卓越往往出自人类的艰辛[22]。
2.重视意义的诠释。通识教育不是给学习者灌输各种事实性知识或者技巧性知识,而是要引导学习者从文化形式中发现人之生存与发展的使命与意义。这是因为文化哲学所建构的世界不是事实性的世界,而是意义世界。卡西尔指出,文化哲学不仅仅要分析各种文化形式,更需要思考展示在各种文化形式之“画廊中的图画的意义何在”[23]。为此,通识教育需要将知识与人类的生存关联,从人类文化价值追求的高度来重新理解和诠释知识。例如,有关伦理学与职业道德的思考,可以把“幸福”作为伦理学思想梳理的核心脉络,引导学习者在学习人类伦理思想史的过程中感悟“幸福”的真谛。同样,有关中西哲学的探讨,也应该围绕人的存在境遇与人生境界来梳理,使哲学成为生存的智慧之学。总之,从生命、生存的高度来进行知识意义的诠释,既体现了通识教育之融通的意蕴,也能够真正促动学习者的生命感悟。
3.凸显对话的观念。通识教育强调融通、通达,因此通识教育的教学实践要格外重视不同学科、不同知识之间的对话。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看,不同的学科与知识都具有其独特的品性与结构,它们是“不可通约”的,这种差异性意味着学科之间融通的纽带不可能是某种实体性的知识,而只能是创造性的对话。通识教育的教学实践不是知识的陈述与灌输,而应该理解为“召唤”“对话”与“敞亮”,即“召唤”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出场”,让他们的思想从“独白”走向“对话”。可以说,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思想之间所蕴含的隐匿的对话主题与对话机制,这是通识教育最引人入胜的亮点。
作者:苏鸿 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向明.对通识教育有关概念的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3):64-68﹒
[2]黄俊杰.21世纪大学通识教育的新方向:生命教育的融入[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4(5).
[3][4][19]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4,39,43,124.
[5][6][20]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1,142,172.
[7][23]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9,38.
[8]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822.
[9]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102-109.
[10][13]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0,56.
[11]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9﹒
[12]刘小枫,陈少明.古典教育与自由教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14]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
[15]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66.
[16]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9.
[18][21]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58,253.
[22]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