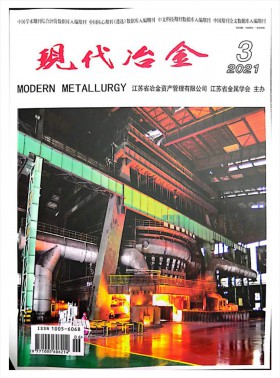作者:郭洪雷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小说修辞①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晚清到“五四”,这一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在小说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小说家虽然都在利用转型中逐渐生成的各种修辞成规,但他们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加之中国现代修辞学创建之初,“受辞格派影响较深”②,重微观,轻宏观,以“修词”代修辞,影响了小说修辞理论的发育,使得中国小说修辞的现代转型未能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如果我们能够从小说修辞角度入手,重构现代小说研究的修辞之维,不仅可以澄清现代小说修辞意识的成长脉络,还可以使原本不被重视的论争获得新的阐释,使其理论价值得到彰显。
一1902年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鼓吹“新民”;沿承这一启蒙思路,同年11月他又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③虽然没有统计,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段文字是梁启超文章中被频繁引用的段落之一。重复率最高的是“新”,梁启超强调的是“新”,引用者看重的是“新”。小说所以能“新”,能使之“新”,着力点终在“支配”二字。然而,在梁启超修辞激情感染下,研究者却放过了“支配”二字,也就无意间错过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修辞之维。梁启超以“新民”为依归,以“支配”为枢轴,描述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熏”、“浸”、“刺”、“提”。
对于“四力说”,以往研究多取径接受美学、心理学、传播学,虽褒贬不一,多角度阐释还是揭示了“四力说”内涵的丰富和复杂。“四力说”之关键在“支配”,梁启超正是从时空、渐顿、内外等方面描述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解释“四力说”须结合梁启超的思想背景和知识构成,尤其要重视其描述所用之话语、例证和运思方式。梁启超自言其论著,“往往推挹佛教”①。他以“应用佛学”推许谭嗣同②,而他自己论著所遵循的恰是将佛法灌注于现实的“应用佛学”。明乎此,其借鉴唯识学理,选取佛经例证,来阐发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方式,也就可以理解了③。梁启超习佛而不佞佛,熟谙佛史而又能放眼欧美,他正是通过佛教辩难与宣教,通过对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学艺”的了解,来认识小说本身的修辞力量,来描述小说修辞的运作肌理和效果的④。梁启超的文章详于描述小说“支配”人道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则将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并强调“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说服方式”⑤。“支配”与“说服”虽词色不同,但都强调修辞运作方式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视野开阔,由政、教两端认识到小说所具有的修辞力量,他还身体力行,创作了一部充满演说与辩论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但他毕竟没有直接使用“修辞”一词。从现有资料看,首先直接使用修辞学来探讨小说的是恽铁樵。1915年,恽铁樵在《小说月报》发表《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一文,从五个方面立论,其中第五项认为,中国作者没有系统的修辞学训练,在小说的“结构意趣”方面不及国外作者。恽铁樵的论述有三点值得关注:(1)阐明修辞学三原则:理、力、美。其中“理”是关键,意近古文家之“提挈剪裁”;(2)为文者以词藻自炫,饾饤满纸,有背“修辞公例”;(3)小说为文学,不能违背“修辞之公例”⑥。从文章看,恽铁樵对修辞学的理解肯定存在误读,对小说修辞的论述也颇为粗糙,但他的理解比较完整,他对小说中微观修辞和宏观修辞的自觉区分,尤其值得肯定。从现有资料我们很难推断恽铁樵对修辞学的论说源出何处,他虽触及了修辞学训练对小说创作的意义,但终究是偶然论及,未能充分展开。直到1922年在《文学旬刊》上,郑振铎与宓汝卓就小说要“写”还是要“做”的问题展开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才得到系统思考。
二1922年4月,沈雁冰在《文学旬刊》撰文,批评当时短篇小说太过“执板”,缺少变化。他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以做诗的态度去做小说”,创作全凭一时灵感,缺乏构思和修改;二是不尚实地考察,对人生世态的描写多是书上读来的,“不是自己捉来的”⑦。文章发表后,很快有人跟进讨论。先是宓汝卓致信主编郑振铎:“近来有许多人主张以做诗的态度做小说———这就是说小说也是‘写’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旧文人以‘做小说为游戏’的一种反响,并不是做小说的‘经常大道’”。并认为像叶圣陶那样的“写”出的作品,“我们与其称之曰小说,无宁称之为散文诗呢。”郑振铎复信说,原来与朋友口头讨论过小说“写”与“做”的问题,小说虽结构复杂、情节曲折、人物众多,但他与叶圣陶还是坚持小说是“写”下的,不是“做”出来的。“因为极端的无所为的客观的描写的小说,决不是好小说,而且也没有做的必要。凡是做小说至少也要有极深刻的观察,极真挚的欲诉的情绪,或欲表现自己的冲动,才能去写。”他在信末总结说:“小说的灵魂,是思想与情绪,如果没有要说的话,没有欲吐的真情,就使极力去‘做’小说,也是‘做’不出来。在艺术方面讲,小说描述的好坏,也不一定靠‘做’,艺术手段高,涵养有素的人写出来就是很好,没有手段的人虽是努力的‘做’也是不会好的。”⑧针对郑振铎的答复,宓汝卓发表长文《关于小说“做”的问题》(连载于《文学旬刊》第42、43期),对郑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反驳,并申述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次讨论,以往关注不多,且认识不一:陈平原认为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概念本身相当模糊”⑨;严家炎则肯定宓汝卓的观点,认为“可供小说家和研究创作心理学的学者参考”○10。如仅从这次讨论本身看,不仅概念相当模糊,讨论的前提及许多相关问题也都不够明确。我们只有弄清讨论的背景,才能揭示其内涵和价值,而这个背景就是在《小说月报》展开的“自然主义的论战”。1922年2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沈雁冰在答复周赞襄的信中指出:“一向落后的我们中国文学若要上前,则自然主义这一期是跨不过的。”由此引起大家关注。同年5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开辟“自然主义的论战”专栏。论战持续近半年,1922年7月,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发表长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可视为对论战的总结。《小说月报》与《文学旬刊》是“姊妹”刊物,了解《小说月报》上的“自然主义的论战”,可以澄清以下事实:(1)小说“写”与“做”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论战”在小说创作技巧层面的延伸;(2)就讨论前提看,沈雁冰《创作坛杂评:一般的倾向》对当时短篇小说创作的批评和分析,与他对“自然主义”的倡导紧密相关。宓汝卓所持观点,既受到了沈雁冰的影响,也是自己的独立思考①;(3)郑振铎所谓原来与朋友口头讨论,其中应包括沈雁冰、谢六逸、叶圣陶等人,以上诸人虽同为文学研究会中坚,但他们对提倡“自然主义的文学”存在分歧。讨论中,郑振铎接受了沈雁冰的部分意见,承认小说“写”前应注意构思,写后注意修改。#p#分页标题#e#
三明确了上述讨论的背景和前提,为我们揭示讨论的理论内涵提供了帮助。郑振铎与宓汝卓都承认小说创作中修辞问题的存在,并且在反对“纯客观描写”和“支支节节地字斟句酌的做”的问题上,观点也是一致的。而这个一致的达成,主要来源于论战对“自然主义”本身存在问题的反思。论战中沈雁冰在答复周志伊的来信时就曾指出:“自然派文学大都描写个人被环境压迫无力抵抗而至于悲惨结果,这诚然常能生出许多不良的影响,自然派最近在西方受人诟病,即在此点。”他还引用周作人的观点,认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②。后来沈雁冰对“纯客观描写”虽有辩护,但他还是承认“左拉主义”的创作态度“是很不妥当的”③。在小说修辞学论域内,对“纯客观描写”有着深刻的质疑和批判④,它背后所呈现的创作态度,有悖于小说修辞的基本伦理精神。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郑振铎、宓汝卓对小说修辞理解存在很大分歧。郑振铎坚持小说创作中修辞介入的绝对性和必然性,强调“写”具有合理性,强调小说修辞运作中情绪、情感的作用和意义,反对只重局部的修饰而影响情绪的自然抒发,影响小说修辞的整体效果。而宓汝卓所谓的“做”,不仅针对当时小说“太过诗化”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了如何处理情绪、情感,如何处理狭义修辞与广义修辞的关系等问题。
在当时的小说理论和批评中,从修辞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出发,来思考小说创作问题的很少,而这恰是“做”的关键所在。宓汝卓写道:“我所主张的做,是先要有感情的挑拨的做;是尽量应用心理学上的原则和艺术上的技巧使固有的情绪格外具体化的表现出来的做。是努力分析自己的情绪,使读者格外容易感受———格外容易动人的做。”显然,他所论不是针对修辞主体而言的,而是指凭依接受心理,施展艺术技巧,通过对作者情绪的处理,来调动读者的情绪。这是他与郑振铎的最大不同,而郑振铎所论是从修辞主体出发的。文中宓汝卓还以苏秦、张仪的政治修辞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在宓汝卓看来,纵横家游说诸侯,仅有好的愿望、好的计谋,未必就被采纳,他们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出言有方”⑤。也就是说,包括政治修辞在内的任何修辞活动,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必须考虑受众。这样,在宓汝卓强调的“做”中,读者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存在,还是小说修辞内部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宓汝卓对当时小说“太过诗化”的批评,显然是受沈雁冰的影响,通过观察和比较,宓汝卓认为,“五四”以来“以诗的态度做小说”的主张在青年作家中影响很大,“但我现在觉得这种趋势只能够为真文艺开一条进行之路,绝非做小说的经常办法,这种‘以诗的态度做小说’的趋势,不过是由‘雕刻字句’进于‘控御情感’的一种过渡罢了”⑥。通过对叶圣陶的《一生》、徐玉诺的《遣民》的分析,宓汝卓认为“诗化”不过是作家能够采取的诸多策略之一,具有过渡性,并非“经常办法”,只有对小说所涉情绪、情感进行有效控御,在一种“人为”的、跳出特定情感之外的“操作”中,小说艺术才能走向成熟,达到理想的修辞效果。
就本质而言,五四新小说普遍采用的诗性修辞,是一种依附性修辞,诗歌毕竟不同于小说,二者“杂交”可以产生新的文体形式,但二者在语言和体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等文类中,诗的语言最具艺术性和独立性,而小说的语言则是“散文化”的,具有日常用语的实用性。正如托多洛夫所指出的那样,实用语言在自身之外,在思想传达和人际交流中找到它的价值,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相反,诗的语言在自身找到证明(及其所有价值);它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不再是一个手段”①。这意味着,诗歌语言存在着抑制交流与对话的因素,诗歌语言的“表达意向”、“自在目的”,决定了诗歌语言不假外求,在自身中寻求审美价值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它与小说语言之间的区别。五四新小说往往借重中国古典诗文的抒情传统,追求小说诗化,从而在修辞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独语”倾向。宓汝卓主张“做”小说,强调“用心理学上的原则和艺术上的技巧”,使得作者与读者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正是看到了诗歌与小说在修辞方式上的不同。他以《三都赋》和《战争与和平》为例,来说明这种区别,认为后者成了世界名著,前者却成了“脂粉堆成的死美人”,主要是因为“前者是支支节节的斟句酌字的意图嚇人的做,后者是运用正真的艺术手段志在充分传染自己的感情给别人:这一些区别罢了”②。宓汝卓举例未必恰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三都赋》中大量的偏词僻字,阻抑了后人对作品本身的欣赏,无法体会其中情感的传达。
四这次讨论还涉及小说修辞中处理情绪、情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郑振铎、宓汝卓二人所论有错位,也有分歧。郑振铎更钟情于传统文人作文吟诗“提笔立就”、无所点定的自然潇洒。他反对雕琢,反对“支支节节”、“句斟字酌”,因为这样拘泥于局部的调整与修饰,会破坏表达的自然流畅,也就破坏了传统诗文的情调和境界;宓汝卓也反对“支支节节”、“句斟字酌”的“做”,反对局部的调整与修饰,认为那样不过是传统诗文的炼字析句,与他所说的“做”有本质不同。他认为“做”是指OP-ERATION(操作)。他在文中写道:“我所主张的‘做’,并不是字斟句酌地做。我以为情绪有发展,挥发,分析,具体化的必要,这种将自己的情绪开展,挥发,分析,具体化,企图将自己的感情表现得格外强烈,企图别人了解,感受我们的情绪,格外深厚的手续OPERATION,便是我之所谓的‘做’了。”③这里所涉及的情感控制是小说修辞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梁启超的“支配”异曲同工,同为作者操控读者的方式方法。宓汝卓主张的“做”,主要是指作者通过对自己情感的有效节制、调配,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技巧和手段,成功左右读者的情感变化和情绪反应,最终顺利地达到自己的修辞目的。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对此多有论述,如他在论述“作者的声音”的问题时,将“控制情绪”作为作者通过议论控制读者的主要手段之一加以探讨。他写道:“作家只须努力将戏剧化的事物的本质揭示出来,方法则是通过提供确凿的事实,或者建立一个观念的世界,或者把细节和这些观念联系起来,或者把故事同普遍真理联系起来。作家努力使读者对材料的同情或超脱程度同隐含作者保持一致,实际上,作者是在仔细控制读者对故事情感介入的深浅或情感距离的远近。”④#p#分页标题#e#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控制读者情感、情绪的方式和方法是多样的,议论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宓汝卓以叶圣陶的《一生》为例,来说明小说中作者对情绪的“控御”。叶圣陶为了要表现乡下妇人非人的生活,“他只描写那个妇人如何被厄于翁姑,如何逃走……但我们看完了,便悠然地发生一种哀感”。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正是因为作者使用了“哀感之挑拨”。宓汝卓认为,哀感情绪本身十分简单,本没有什么可写的,“作者如不尽量把它展开,分析,将如一幅捲拢了的西洋名画,究竟不能让读者领略到丝毫之美”⑤。相反,叶圣陶的另一篇小说《恐怖的夜》,由于只是任情的“写”,不能对小说中的情绪、情感进行有效的“控御”,到了后半截则给人窘迫勉强之感。宓汝卓认为:“这是因为作者落笔前虽然有些情感,落笔后却仅仅靠‘写’。感情亦是暂时的,作者不能因势利导的把它开展,一霎时就会消灭。及到感情消灭了,文章还没有做好,这才要勉强窘迫了!而且仅仅靠写的作品,情绪常常是愈做愈弱。作者兴致完了,笔就搁起来了……决不能达到‘感情传染’的目的。”①通过两篇作品的比较分析,宓汝卓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小说修辞中“控御情绪”的问题。
一方面为了显示情绪控制在文学中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在论争中提供成功进行情绪控制的范例,宓汝卓又对《葬花吟》的情绪控制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分析黛玉如何进行“情绪的展开”、“情绪的挥发”、“情绪的分析”。在宓汝卓看来,《葬花吟》虽为诗歌,但正是因为作者有条不紊地控御情绪,才能最终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情感共鸣。他认为这样的“做”,只会“因文生情”,不但不会减弱破坏作品的情感表达,而且使小说中的情绪、情感带给人众流归海、蔚为大观的感觉,可以使读者在“文虽尽而情弥长”的地方,领受到更深的印象。相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和修辞伦理,宓汝卓将小说中的情感处理,理解为“因文生情”,在当时颇为难得。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将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分为两类:“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在刘勰的观念体系中,“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自然有真伪高下之分。“为情”者简要、真实,“为文”者淫丽、夸饰,虚假滥情。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儒、道二家在情理与文辞关系上,态度十分相近。儒家认为“巧言令色鲜于仁”,道家讲“大音希声”,“大美不言”。刘勰继承了儒、道二家有关情感真伪的伦理精神,强调情正、理定为“立文之本原也”。刘勰在这一问题上所体现的伦理态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影响深远。
宓汝卓所谓的“做”小说,在情感处理上强调“因文生情”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小说修辞中,修辞主体的情绪、情感与小说中叙述者和人物的情绪、情感虽然相通,但毕竟不同。郑振铎、叶圣陶主张的“写”,更多是从前者出发,而宓汝卓强调的“做”更多指向主体与客体的有效沟通。宓汝卓所强调的“做”,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差别。第二,在小说的情绪、情感处理中,为了达到理想的修辞效果,允许必要的、合理而又合目的的虚构和想象。而这一点不仅反映了宓汝卓本人的理论自觉,而且反映了五四时期小说家在修辞伦理上突破传统的束缚,试图营构新的修辞伦理价值谱系的自觉意识。宓汝卓以自己的小说《破袜》为例,来说明在新的伦理视域中,虚构与杜撰的合法性。《破袜》的后半段是作者隔了半年之后加上去的,而大家觉得“比较的最能动人”。“前面一段倒还是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倒还是因为欲吐的感情侵通我写的。这最末一段的事实全是虚构,而落笔描写时又没有怎样强烈的感情;何以写来反较为动人呢?”宓汝卓解释其中的原因时说:“文学家仅仅有真挚欲吐的感情,未见得写来就能动人。欲吐的真情,不过是‘小说的河水的泉源’罢了”,“泉源”要想能够奔腾澎湃,汇为巨观,只有通过“做”,通过冷静的OPERA-TION(操作),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的。
从1902年到1922年,中国现代小说处于发轫期,小说理论和批评尚未完备,不可能对小说修辞进行系统思考,更不会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剥离出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层面。但是,通过考察梁启超的“四力说”,恽铁樵对“宏观修辞”和“微观修辞”的认知,以及宓汝卓与郑振铎对小说“写”与“做”的辨析,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依稀可辨。特别是宓、郑之间的讨论,其意义不仅表现为反思五四新小说存在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它从技术层面触及了五四时期一代小说家长于短篇,短于长篇,工于“修词”,拙于修辞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成熟现代长篇的理论吁求,在此已“渐露机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