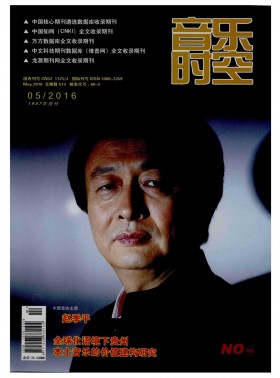作者:李新亮 单位:南京大学
自1969年托多罗夫提出“叙事学”这一术语以来,叙事学逐渐成为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显学。托多罗夫的叙事学主要探究叙事的本质、形式和功能,并进而探索故事背后的普遍结构。随后,热奈特将叙事学的研究继续推进,他在1972年发表的《叙事话语》更是奠定了叙事学研究的范式。如果说托多罗夫叙事学所关注是叙事文本的宏观方面的话,那么,热奈特更关注的叙事文本中的微观方面,他的叙事理论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关注故事和叙事文本的关系,诸如叙事话语的时序、语式、语态等。他所运用的叙事时间、叙事视点、叙事声音等术语也成为我们分析现代小说的重要理论工具。叙事节奏同样是叙事学中的概念,虽然当代叙事学更多地关注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视点和叙事声音等方面,但叙事节奏是叙事学题中应有之意,是其无法避免的研究对象。因为凡有叙事必然会存在节奏,无论是表现在叙事文本的叙事语流层面,还是表现在叙事情节及叙事结构层面,叙事节奏的轻重缓急对叙事功能产生着十分重要影响。
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大区别是更加关注小说形式的探索。形式本是区别各种艺术门类的基本要素,而现代小说将小说形式提升到小说的本体地位,由以往的重视“写什么”转变到重视“怎么写”。现代小说为了丰富艺术的表现力,向其他艺术门类借鉴创作手法已经为一种常见现象,诸如诗性、绘画性、建筑性、音乐性等均进入了现代小说的创作实践。有很多现代小说在叙事节奏上体现出音乐节奏的特征并展现了很高的艺术表现力,这构成了现代小说音乐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了现代艺术门类之间相互位移和借鉴的可能性。
一、音乐节奏与叙事节奏
节奏本是个音乐术语。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节奏是“音乐的时间形式”。《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为:“乐音时值的有组织的顺序,是时值各要素————节拍、重音、休止等相互关系的结合。强弱、快慢、松紧是节奏的决定因素。其作用是把乐音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体现某种乐思。”[1](P314)从词源上讲,节奏表示流动之意,考察西方语言中的节奏一词,德语“Rhythmus”,法语“Rhythme”,意大利语“Ritmo”,英语“Rhythm”,都出自表示可以计算的运动、计量、均衡之意的希腊语“ρυθμζ”,而这个词又出自流动之意的希腊语“ροη”一词。节奏之于音乐至关重要:“节奏赋予声音的混沌体以生命力。没有节奏,音乐就不能表露出活动力。有了节奏,音的排列才能产生丰富的生命力,显露出惹人注意而又有意义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来。”[2](P80)音乐节奏的构成要素主要是节拍、速度和力度。节拍是时间间隔中强音与弱音的周期性循环,通俗地讲就是“拍子”。如,2/4拍即是每个音乐小节有两拍,以强弱的次序反复出现直至音乐结束,3/4拍则表现为强弱弱的形式,4/4拍则表现为强弱次强弱的形式。节拍规范了音乐的秩序,只要找准了节拍,就一直循环下去。节奏的速度主要是指音乐在演奏或歌唱过程中节拍的快慢,一般会根据歌曲的内容和情感表现来调节速度的快慢。节奏的力度则是指乐音的强弱程度,经常会在某些语音上加重或弱化发音,以此来表现情感。音乐的力度有着魔力般的音响效果,通过力度的变化,音乐可以表现雄伟悲壮、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也可以表现温润绵长、如泣如诉的婉约风格。节奏之于音乐的表现是最重要的,如果节奏变了,音乐的内容和形式随之都发生改变。在音乐作曲中,经常有某首歌曲的节拍慢了一半,或被拆分成两段,就会变成了另一首不同的歌曲。音乐节奏有很强的感染力,《礼记•乐记》曰:“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前苏联音乐理论家玛采尔指出:“节奏善于异常有力地、直接地、几乎是从生理上感染广大听众:鼓声甚至可以从情感上感染完全不懂音乐的人。”[3](P34)可以说,节奏是音乐最为本质的特征。当然,节奏并不是音乐所独有的现象。放眼浩瀚的宇宙时空,“节奏是宇宙中自然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自然现象不能彼此全同,亦不能全异。全同全异不能有节奏,节奏生于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寒暑昼夜的来往,新陈的代谢,雌雄的匹配,风波的起伏,山川的交错,数量的乘除消长,以至于玄理方而反正的对称,历史方面兴亡隆替的循环,都有一个节奏的道理在里面。艺术反照自然,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在造型艺术则为浓淡,疏密,阴阳向背相配称,在诗、乐、舞诸时间艺术,则为高低、长短、疾徐相呼应”[4](P108)。回归到日常生活,吃饭、行走、呼吸都需要节奏。简而言之,凡是具有时间性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具有节奏。
小说作为叙事体艺术,是语言在时间中的运动形式,自然也有叙事节奏。语言学家认识到了语言的音乐节奏重要性:“语音组合具有独立的节奏和音乐形式,借助于这种形式,语言把人带入了另一个领域,强化了人对自然中美的印象,但语言并不依赖于这些印象,它只是通过语声的抑扬顿挫对内心情绪产生影响。”[5](P74)同时,许多文学家和理论家尤为重视语言艺术作品的叙事节奏。朱光潜认为:“声音节奏在科学文里可不深究,在文学文里却是一个最主要的成分,因为文学须表现情趣,而情趣就大半靠声音节奏来表现……我因此深信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6](P221)韦勒克也持同样的看法:“这种节奏如果使用得好,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本文;它有强调作用;它使文章紧凑;它建立不同层次的变化,提示了平行对比的关系;它把白话组织起来;而组织就是艺术。”[7](P175)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正确运用速度节奏就会产生正确的情感和体验,反之则有损情感的表达。”[8](P170)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节奏是理解诗句的重要方式:“节奏运动是先于诗句的。不能根据诗行来理解节奏,相反应该根据节奏运动来理解诗句。”[9](P122)申丹则将叙述节奏引入到对小说的研究之中,她认为:“我们在研究叙述节奏时,也应关注文字本身的节奏,在一些故事情节淡化的现代作品(如意识流小说)中文字节奏尤为重要。”[10](P198-199)其实,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叙事节奏问题,在这方面,金圣叹论述得最为全面和深刻,例如“急事缓写”等策略已成为小说节奏理论的定论。#p#分页标题#e#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节奏都具有音乐节奏的特性。那么,如何来界定现代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呢?换句话说,现代小说中怎样的叙事节奏才是可以称之为音乐节奏的呢?正如节奏之于音乐的重要性一样,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就是必须要通过节奏的变化对小说的审美形式、叙述结构、主题表达产生直接的影响。曾有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节奏美做过总结,主要从情感节奏、对话节奏、动作节奏、情节节奏、结构节奏等几个方面论述。[11]但是,这种论述方式依然是从小说本位出发的,而不是从叙事节奏出发的,不免有将节奏比附到小说的各个层面中的浅薄之感。本文将从叙事节奏的本位出发,总结现代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在具体的表现对象上,现代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主要通过小说文本中叙事语流、叙事情节的节奏变化来实现的;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小说的叙事节奏富有音乐性的表现主要是叙事速度和叙事力度的变化。当然,很多小说作品中,叙事速度和叙事力度往往是彼此交融的,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分而述之。
二、叙事速度
叙事速度是现代小说叙事节奏的主要呈现方式。叙事速度的变化带来节奏的张弛有度,由此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表现、主题阐释产生重要的作用。现代小说叙事速度的变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叙事语流的轻重缓急在语言声音层面形成声音节奏,从而产生听觉上的乐感,这是在感官上直接体验到的音乐性。二是通过叙事时间的调控在小说情节层面形成叙事节奏,具体来说,就是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非等时所造成的节奏效果。如果说语流变化所形成的叙事节奏是小说的外部节奏的话,那么,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非等时所形成的叙事节奏则是小说的内部节奏。
(一)叙事语流的速度变化
现代小说通过语流的变化形成叙事速度是现代小说家常用的手段。在现代小说家看来,选择不同的叙事速度对小说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同速度之于音乐的关系一样。悲剧氛围的小说叙事语流大多是缓慢的、回旋的,喜剧氛围的小说叙事语流大多是欢快的、跳跃的。如果悲剧小说的叙事语流按照喜剧小说的叙事语流重写一遍,那么再经典的小说也将是出现不伦不类的面貌。为了有效地实现叙事速度的变化,长句短句相间、相似句式的铺排以及词语和句子的重复是最为常用的叙事策略。鲁迅的小说《伤逝》就是通过这一策略来实现叙事速度的变化。《伤逝》是涓生追思悼亡子君的私语言说,悔恨之心、感伤情调弥漫着整个小说。鲁迅在小说的叙事速度与这种感伤情调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小说一开头就为整个小说定下了回旋的音乐曲调:“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短短一句话,重复三个“我”,以两个“为……”句式铺排收尾,从“我”开始,以“自己”收尾,由此拉开小说的帷幕。小说主体部分是对子君的追慕缅怀,分为相恋、同居、分手与悼亡四个部分。其中,每个时期的叙事节奏又都随着涓生的情感变化而变化。鲁迅在叙事中经常重复一些话语:“多次的重复减慢了旋律的速度,赋予句子以一种忧伤的韵律。”[12](P119)同时又推进小说情节的向前发展,有学者对鲁迅的话语重复进行综合分析后排序,做出如下的语流变化图式[13](P143-144):①②→②①③→③①④→④③⑤→⑤③→……③⑤⑥→⑥④通过图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环套中间都有一组小回旋,环套和环套之间或并联或套扣,结成连贯畅达的一体。人物的种种情绪在小回旋中复沓,在大环套中呼应、升腾、交织和宣泄”[13](P144)。显然,这是鲁迅的刻意为之。这样做就造成了行文舒缓、欲进还退的小说节奏,回旋地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叙事速度赖以句式的长短交错形成的文气,同时也赖以语言的停顿和间歇。如果再调动排比、顶针、回环、对偶、反复、层递等修辞格,节奏感就会更加凸显。例如,王蒙的小说《春之声》,为了表现社会现代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破冰之后的欣欣向荣,主人公岳之峰坐着闷罐车却浮想联翩,小说的叙事节奏一直是欢快的,如为了展现现代生活的快速节奏及岳之峰回家的急切心情,小说这样写道:“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不管有多么艰难。哞,哞,哞,快点开,快点开,快开,快开,快,快,快……”小说的叙事节奏在语言的音节越来越短,造成了这样的艺术效果。同样更富有欢快节奏的句子还有很多,如:《春之声》中“车声小了,车声息了。人声大了,人声沸了。……是山泉,榆钱,返了青的麦苗和成双的燕子吗?”这一段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有学者指出,这样的句式有双重的节奏效果:一是语言的音乐性节奏,二是内容的联想性节奏。[14]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富有音乐性的叙事节奏有力地传达了主人公的内心精神世界和小说的主题表现。
(二)叙事情节的速度变化
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非等时所形成的叙事速度,是热奈特在分析《追忆逝水年华》时提出的概念。在他看来,“无论在美学构思的哪一级,存在不允许任何速度变化的叙事是难以想象的,这个平常的道理已具有某种重要性:叙事可以没有时间倒错,却不能没有非等时,或毋宁说(因为这十分可能)没有节奏效果。”[15](P54)这是本文研究现代小说叙事速度变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小说作为一个叙事的文类,至少要包含一个双重的结构,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将之分为故事(fabula)与情节(sjuzhet),还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将之分为故事(histoire)与话语(discourse)。说到底,小说是一个关于讲述的活动,这就要尤为关涉到讲述者与听众或读者的关系,因此,在叙事上自然有详略与快慢。通俗地讲,就是故事时长与小说文本长度的对位关系。较之语流变化形成的叙事节奏,这一叙事节奏应用的也最为广泛。当然,只要有叙事就会存在叙事上的非等时及叙事节奏,这也并不是说所有叙事上的非等时形成的节奏都具有音乐性,只有那种节奏效果不仅带来了某一段落的和谐,更体现于整个文本的和谐,充分并恰当地利用此效果会更有利于情感主题和思想的表达,这才是一种音乐性的叙事节奏。热奈特为了具体阐释这一理论,他将小说叙事速度的模式分为四种类型,即概要、停顿、省略、场景,并且直接将小说的叙事节奏与音乐节奏做了参照:“这四个关系在(尚未诞生的)文学史有一天将研究的演变中变成了小说速度的标准形式:有点像古典音乐传统在无数可能的演奏速度中分了几个标准乐章,如行板、快板、急板等,他们连接和交替的关系在近两个世纪中支配了奏鸣曲、交响乐和协奏曲的结构。”[15](P59)无独有偶,米兰•昆德拉同样注重小说的叙事速度,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理论呼唤,也是一种创作实践。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夫子自道:“一章就是一个旋律。而一节就是节拍段。这些节拍段或长,或短,或不规则持续。这便把我们带到了速度问题上。我的那些小说中的每一节都能标以音乐指示词:中速、急板、柔板,等等。”[16](P85-86)在创作中,他总是寻找合适的叙事节奏来表达小说的主题。在小说《生活在远方中》中,第六章的主题是渲染和平与同情的气氛,于是在节奏上他选择了柔板,而第七章的主题是为了创造被刺激的残酷的气氛,于是,在节奏上他选择了急板。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在创作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小说的节奏,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要表达很少的事件,气氛是平静而伤感的,在节奏上自然是极为轻松的柔板,而在此之前的一章《伟大的进军》需要表达很多的事件,气氛是粗暴的、厚颜无耻的,在节奏上自然需要极快的速度。昆德拉认为这样的节奏变化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这个最后的对照中,我想集中小说所有的感情力量。”[16](P87)可见,通过小说叙事节奏变化形成的强烈对比可以更为有效地突显小说的主题。#p#分页标题#e#
三、叙事力度
音乐的力度是通过强调乐音的强弱来实现节奏的变换,叙事力度并不同音乐的力度一样从而特别强调语音的强弱关系。因为,仅仅强调语音的强弱关系是一种绝对的音位学上的对位,并不适用于现代小说的叙事节奏。现代小说叙事力度的音乐性主要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比较,现代小说叙事的力度是指对小说叙事中情感强弱的控制以及对小说叙事情节中情感基调的把握。通过对小说叙事中情感的力度变化和对叙事情节的力度变化的适当调节,更有助于对现代小说主题思想的表现。
(一)叙事情感的力度变化
虽然小说是一种叙事文本,但叙事中同样也包含着情感,对情感抒发的控制会为小说叙事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叙事情感强弱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语句调控来实现的。语句的拆分、整合与颠倒、音节停顿及声调变化最能有效地突出叙事力度的变化。鲁迅的小说作为典型的音乐性文本,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为了使小说叙事力度能体现出对情感的加强,破句拆分是极为有效的手段。如在《伤逝》中这样的句式极为多见: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这些句子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如果写成“我要为子君和自己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这样的句式,叙事力度就减弱了,情感表现也大为失色。通过将这些句子拆分为几个短句,层层递推,力度渐强,则更能表现“悔恨和悲哀”的心情。音节的停顿同样可以实现这一效果,如《祝福》中总结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句子:“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通过音节的停顿标示,这个长句子的音节停顿竟多达36次。这是鲁迅刻意通过句式来体现对祥林嫂的悲悯之情,在这个句子中没有重音词,所有的力度都是一样的,《伤逝》的例子是短句子加强了叙事力度来表现情感,而这个长句子则是弱化了叙事力度来表现情感。对于祥林嫂的死,什么样的叙事力度能够表现得出呢?她的两度嫁人,无数次地念叨被狼叼走的阿毛,这样曲折悲惨的人生也只有这样低沉呜咽的长句子能表达得出。声调的变化也是叙事力度表现的重要手法。平声字在叙事力度是弱化的,仄声字在叙事力度上是强化的。为什么强调《祝福》的第一句话?我们常说第一句是最能奠定情感基调的,鲁迅以如此情感强烈的叙事力度开篇还是很少见的。
(二)叙事情节的力度变化
叙事力度还表现在小说的情节进程中。对小说叙事进程的整体基调的把握则更为重要,因为,小说叙事总要有个开端、发展、高潮、结尾,怎样使故事的进程更为跌宕起伏,更为吸引读者的关注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也有些小说没有结尾,保留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但是,故事的进展总是要有的,即便是在极力消解故事性的最为极端的现代小说中,小说的情节依然还能被理出清晰的脉络。例如,当代小说家余华就经常在小说叙事中有意识地借鉴音乐力度的处理方法。余华在《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一文中说:在听了巴托克和梅西昂的音乐后,“音乐开始影响了我的写作,确切的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17](P8)尤其是在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第一乐章的叙述,让余华认识到音乐叙述中“轻”的力量,由此带来文学叙述上的启发。小说叙事与音乐叙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是通过叙事或声音的慢慢推进,将情节(或情感)逐步提升,最后达到高潮。音乐的高潮是“在一条旋律中,或一首大型作品中的最高音,或者感情的焦点。”[18](P391)小说叙事的高潮同样是叙事力度最强的时候。如何处理小说的高潮一直是小说家们思考的重点。余华曾说:“高潮的来临常常意味着叙述的穷途末路。”[17](P40)如何在这末路的叙述面前实现峰回路转呢?余华从音乐中得到的启发就是轻的叙事力度的运用。在余华的小说中,这种叙事力度的转变几乎成了一个模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两部苦难叙事的小说。在《活着》中,福贵经历了败家、战争、丧子、丧女、妻亡、女婿亡故,到最后,唯一的外孙也死了。这样的叙事情节仿佛是在情感蓄势,慢慢积累,到最后迸发。余华很聪明地从音乐力度中学到了处理方法,在叙事力度不断加强的进程中,到最后的处理又是那样的平静,福贵一个人牵着老黄牛在犁地,平静地念叨着一个个逝去的亲人。这是叙事力度的恰当处理,任何重的力度也无法表达的情感,而轻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一叙事又回到了小说的主题:活着是什么,为何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前后讲述了许三观11次卖血的经历,这是许三观苦难人生的缩影。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每次卖血都有不同的反应,在叙事上如同11个情感力度各不相同的乐章。尤其是在小说第28章集中写了五次卖血,可谓达到叙事力度的最强时刻,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也曾同余华听音乐一样思考,小说将如何讲述最后一次卖血,用什么样的叙事力度。最后一次卖血是第12次,不过没有卖成,卖血已经禁止了。但是,许三多卖不了血却忧心忡忡:以往的卖血都解决了家中的紧急情况,如今不能卖血,“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小说以这样轻的叙事力度结束。余华的小说无论在想象上如何飞升,在叙事力度上如何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回归大地。音乐的确给予了余华极为出色的小说叙事技巧。综上所述,现代小说通过叙事节奏的巧妙运用的确可以更为有效地增强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无论是现代小说叙事理论还是现代小说作品都给予了有力的证明。现代小说的叙事节奏模仿和借鉴音乐节奏将在未来的小说有着更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