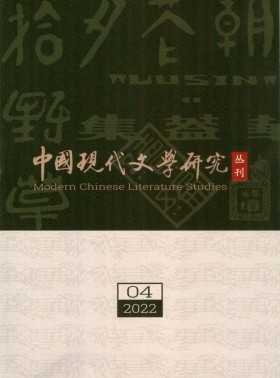关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发掘其特色,有人认为,贵州文化的主体特征是山地文化,也有人认为是民族文化,还有人认为是高原文化或森林文化。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贵州文化是一个多元、多样、多层次“多元一体”的文化系统。史继忠认为,“从总体上看,贵州地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复杂的文化现象。在贵州文化构成中,汉文化固然占着主导地位,但它不是纯粹的汉文化,而是夹杂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存在,而且少数民族文化也并非一种,而是分属苗瑶、百越、氐羌和濮僚文化体系,并演化出多种民族文化,如苗文化、布依文化、侗文化、水族文化、彝文化、土家文化等等”。[1]146
从地理位置来看,贵州又是典型的内陆省份,深受周边文化影响。在贵州,黔北一带明显属于巴蜀文化的范围,黔东一带颇受荆楚文化的影响,黔南及黔西南与两粤文化多有共同之处,而黔西北和黔西南的某些地区又近乎滇文化。事实上,用“多元性”来概括贵州文化当然说得通,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元化的特征,只是贵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多元”,既是指文化来源的多源性,也是指“多来源”文化的共存。正因为存在着“多来源”文化的共存,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固然有迹可循,但呈现更多的是多种文化的“共生共荣”。所谓“共生共荣”指的就是多样的文化至今仍然活着,它们各自以其传统为母本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而向前发展,在“一体”中各显个性。这说明贵州地域文化是一种文化宽容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也不排斥其他文化的生长,各显其长,相得益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多元一体”在贵州这个特定环境中,以“多元”体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以“一体”体现各种文化共处一地的和谐与协调。贵州文化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共荣共生,给这里的各种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和权利,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虽然也相互制约不能让某一文化获得长足发展而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文化权威),所以各种文化现象都得以延续下来。在这里,传播与传承保持着相对的平衡,各种文化之间也维系着某种均势。尽管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但持续的时间不过五六百年,强度也远不如中原或江南地区。因此,相对传统主流文化,贵州地域文化更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而作为由不同的行政区划切割拼合而成的省份,几种地域文化在贵州交汇,因其皆成弱化状态,而且又继续受到四周文化的影响,因而这些文化并未融为一体,仍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只不过范围大小有所伸缩,在贵州境内有所交融而已。更有在其他区域已无迹可寻的“文化孤岛”现象的遗存,许多在中原早已失传的文化却至今仍在这里保存完好,而且始终充满生机,例如屯堡文化。
由此,我们说多元、多样、多层次构成贵州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不错的了,而贵州地域文化与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也由此说开去。关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一个最经典的表述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真正深刻开拓的地域特征中必能找到人性内在的相通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中体现出的主体性创造,必能续人类精神之火,成为世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是,我们择取贵州地域文化不同层面的文化特征,追寻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的缕缕回响。文化特征其一:山地文化“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
这是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馆记》中的一段话,用来形容贵州的地理特征和山势磅礴最恰当不过了。贵州省境内山地和丘陵的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地只占7%,且出露的石灰岩面积占74%,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开门见山”的地方。张晓松在《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中提到:“在贵州,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资源、生产生活条件,都是由这个山地所提供的,这是贵州文化生成的根本和基础,是贵州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依托,山与贵州实在是有着至关重要的生命联系。”山地文化是贵州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斯图尔德指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2]12长时期处于落后生产方式状态下的贵州人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山。他们出行、劳作得翻山越岭,得靠打猎、刀耕火种获取食物;住“干栏”式房屋或石头屋;甚至死后也安葬在石棺中。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低水平的物质生产又适应了简单的文化形态,造成超稳定形态的文化结构和“内循环”的文化发展,由是,“贵州人的文化性格就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贵州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耿直无华、个性倔强;另一方面,山高路险的封闭环境又使得贵州人不善算计、目光短浅、封闭狭隘、满足现状、不求进取、重土少迁,乡土观念极重。”[3]20综上所述,山地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封闭性。对于这种封闭性也应一分为二来看待。因为封闭,就使得贵州文化背负传统因袭的重负少得多,因此又孕育了贵州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与主流文化、周边文化交流、碰撞中,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但也造就了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共生共荣”的局面。诸如:虽然典籍文化相对薄弱,但乡风民俗文化底蕴深厚;虽然代表汉文化的主流文化逐渐落地生根,但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虽然在对待外来文化上采取深拒固闭的大有人在,但满怀热情主动接纳外来文化的仁人志士最终“振臂一呼而改天换地”;更遑论封闭的环境也成就了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他的“致良知”的心学理论正是从贵州走向世界的。
山地文化封闭与开放的二重性是互为消长的,随着交通的发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封闭的因素将逐渐减弱,而开放的特点将日益强化。当晚清以来席卷全国各地的变法维新、倡导自治的图变之风吹进贵州这封闭已久的“山国”时,贵州人以高昂的开放姿态回应着主潮。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贵州一些开明人士就已创办《黔报》、《贵州公报》、《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等地方性报刊。1907年“贵州自治学社”成立,该学社提出“以个人自治说为起点,以地方自治说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说为最终面积”的学说主张。辛亥革命期间宣布独立的“贵州军政府”称贵州乃西南之中心,同时也意识到“黔中向名山国,风气之开,每落人后”这样的地域特征。有感于此,发生期的贵州现代文学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以“开启民智”为鲜明目标,虽然成就不大,但甫一发生,就呼应了时代主潮。文化特征其二:世俗文化贵州是个名副其实的“移民省”,不仅汉族主要是移民而来,就连少数民族也如此。汉族自汉、唐以来,就陆续由中原迁入贵州。大量入住,应该是在明、清以后。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贵州有两次大的汉族移民高潮,一次是调北征南(即调集大量军队平南),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兵平定云南后,指令30万大军屯戍贵州以防后患;另一次是调北填南(即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强迫迁移往贵州等地),清代中叶朝廷征讨播州藩司杨应龙后,引入大批汉人在“苗疆”屯田垦殖。[4]38这样,汉族在其不断向西南扩散的过程中,不但从邻近的四川、湖广移入,也从中原、江南或其他地区来到贵州。而少数民族包括氐羌民族自西而东、苗瑶民族自东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元代又从云南迁来蒙古、回、白等民族,也是从四面八方进入贵州。这种移民大迁徙,最终导致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从而基本奠定了贵州文化“多元会合型”的格局。#p#分页标题#e#
由于上述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粗犷的军人和底层小商贩及农民,他们更倾向于商人阶层文化的世俗性和农耕文化的精神追求,加之贵州本地文化以巫文化为主的强大根基,使得贵州的地域文化,无论精神信仰追求,还是物质文化追求,都显现出鲜明的世俗性。就拿宗教信仰来说,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特征。在贵州,信仰儒、佛、道、基督、伊斯兰教以及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的民众各自奉行自己的信仰,互不干涉。在建省前,贵州许多地方的民众大多信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不多,影响也不大。但到了明清两代,情况有了变化,佛教和道教因统治者的倡导开始兴盛,但仍能与其他宗教并存,贵州境内随处可见的“三教寺”就是宗教信仰“多元共存”的明证,例如镇远古城的青龙洞,不仅有儒家的紫阳书院,也有佛教的中山寺、青龙寺、观音殿,还有道教的吕祖殿、万寿宫、青龙洞、紫阳洞等。贵州的世俗文化根基雄厚,它的底层文化是巫文化,这使得传入贵州的宗教不得不扭曲自己来适应较低层的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不得不采取与当时当地人们的世俗文化相互契合,吸收并接纳本土基础文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改造性传播,从而产生了许多文化变异现象。例如,在佛教原先的文化母体中便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以及儒、道、佛、巫等多种宗教合流的文化新质,而佛教自身原有的某些特点却模糊甚至淡化了。如此一来,各种文化各自的个性特色明显减弱了,而新的一种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性”却增强了,而这些共性都建立在贵州世俗文化的基础上。
即便是世居其地的少数民族,也有着深厚的世俗文化根基。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伯格里注重苗族信徒的世俗生活,他在石门坎创办学校、麻风病医院、织布厂,建筑起教堂、足球场、游泳池,开设了“公益场”,修筑了公路,创造了老苗文,因此仅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使得一个几千年来崇尚“巫鬼”的大花苗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洋教。这种世俗性还表现在对待外来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上,据史料记载,古夜郎国之所以愿意归附汉王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的吸引力,为了得到汉朝锦帛、铁器等先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技术才心甘情愿归附的。到明清乃至民国也是如此,一方面财力上依附中央,“厚赐”则附,无赐则叛。这种世俗功利性折射在人的文化性格上就是重物质,轻精神,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但也对外界新鲜事物保持高度热情,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黔南识略》卷一《总叙》中谈到黔南地区的民性时就指出“大率质野少文,纤啬而重利”。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采风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了贵州人生活的极度贫困,另一方面也深切体会到了保留在这民间世俗文化上的淋漓的生命元气。通过近代报纸我们可以看到,在报刊开拓的公共空间下,社会各阶层虽然始终处在军阀混战的生活困境中,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切照旧。
学校照常开学,商店、药店、书店、报馆照常营业,他们关心战时局势,抨击社会丑恶现象,也可以在“外国要闻”中看看“西洋镜”,在充斥着沉重的税赋、盗抢现象严重、物价飞涨的社会夹缝中活在当下,努力生存。文化特征其三:通道文化贵州作为一个存在、被发现缘于“通道地位”。就地理区位来说,贵州处于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隔河相望。巴蜀与两广的交通势必要经过贵州,湖南通往云南也要从贵州经过。南来北往,东进西出都以贵州为喉襟,这就决定了它在西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尽管秦始皇一统天下,但古夜郎的“自雄一隅”尚无人知晓。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力强盛,这才有了“开三边”这样向外扩张的举措。因要剪灭南越王,需“浮船??江”,夜郎被发现。为了打通巴蜀与夜郎的通道,唐蒙“发巴蜀卒治道”,史称“南夷道”,从此打破了夜郎与中原隔绝的状态。汉代在夜郎地区建立了??郡,因夜郎地区既是巴蜀通往南越的桥梁,又是通往滇国、开辟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后的诸葛亮南征、魏晋六朝设??、建宁、兴古三郡、隋唐设经制州、南宋在贵州进行“川马”和“广马”的交易,至元朝开通滇黔驿道,都显示了贵州作为“通道”的重要性。
贵州单独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意义出现,是在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贵州布政司(成为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之一)开始的。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划在全国也还是比较早的,不但早于东北和西北,就连湖南、湖北当时也还未从湖广布政司分出来。其后的清代十八行省有贵州,民国二十八省有贵州。之所以在多山、贫瘠的贵州建省,明代史学家郭子章在《黔记》中将原因一语道破:“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藏戍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贵州是中原通向西南边陲的要道,历代封建王朝要扩大疆土巩固边陲就必须打开贵州这个通道。从战略角度讲,无论“攻”与“守”,贵州的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明代地理历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中写道:“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襄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飘驰葭明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禁吭且为我所益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曰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明朝统治者通过派重兵驻扎、沿驿道设立卫所、建立都指挥使司直至建立布政使司,牢牢控制了贵州这个战略要地,以平播和奢安两大事件震动西南。
通道地位使贵州改变了过去闭塞的局面,中央王朝开始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中原各地的文化开始源源不断输入贵州,给贵州文化带来新的质素。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业、建筑、交通等都获得长足发展,教育也获得新的生机,全省各地在洋务运动和期间,纷纷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以新知识和新思想开启民智。光绪末年,贵州还办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青溪铁厂和文通书局,在古老的驿道上也出现了民间运输与邮寄。有了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支持,贵州在20世纪初追赶上了国内第一波办报热潮,也为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无以替代的新媒介,开拓了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当然,仍然要看到通道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改变着闭塞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民众遭受着因通道便利带来的“鸦片烟祸”等人为灾祸。在中国近代史上贵州是鸦片烟祸的重灾区之一,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军阀和官吏是造成烟祸的元凶。贵州军阀不仅通过强制人们种植鸦片、贩卖鸦片获取巨额军饷,而且军队中的士兵也普遍吸食鸦片烟。底层民众吸食鸦片更是常常将整个家庭拖入崩溃的边缘,贵州籍作家蹇先艾、寿生等在他们的乡土小说中对鸦片烟祸都有生动的文学描述。文化特征其四:边缘文化当代评论家陈思和说过这样的话,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事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5]这里所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也就是正统文化与边缘文化。上世纪初,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贵州文化无疑属边缘文化。贵州的边缘文化具有双重边缘性的特点。相对于中心地区,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环境来说,都常常是边缘的边缘。由于地处偏僻、山高路险,中央政权往往鞭长莫及,通常会采取羁縻政策或“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来实现统治。#p#分页标题#e#
这里又是典型的“土流并治”地区,这种“双轨制”给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随着流官统治的加强而使中原正统文化扩大传播,另一个方面又给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等边缘文化留下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种文化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形态:既有宗法制下的愚昧落后,又缓慢地向着文明开化爬行;既有传统礼教文化的顽迹固渍,又有鄙野边地的野蛮丑陋。从贵州特殊的历史条件来说,贵州省的行政区划是切割四川、云南、湖南、广西部分地区而成的,因此,贵州地方的生活习性、文化心理、民风习俗多得周边省地之风,社会文化环境并不闭塞。作为朝廷流放迁徙之所,移民和流徙也为这个僻远之地带来了较多的中原文明和传统思想文化。但另一方面,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又造成交通困难,经济落后,社会文明的进度缓慢,所以保留了较多陈规陋习和传统落后的乃至原始的文化意识。这种边缘文化导致文化主体精神不强,虽以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为主导,但边缘文化又对抗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心理及性格往往兼及南北,融汇四邻。“堪称既直爽又婉转,既犷悍又胆怯,既开放又封闭,既自大又自卑,既勤劳又疏懒,既将就又讲究,既愚昧又狡黠,既质实又幽默,既知足常乐又不满足现状。”[6]15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文化主体,在时代大潮的潮起潮落中随起沉浮,可能浮得很高,也可能很快落回潮底。
边缘文化导致文化主体精神不强,缺乏文化自信心,始终处于纠结矛盾之中。一方面企盼了解外部世界,获取外部信息和先进的技术、物质生活资料与管理经验,以改善自身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因害怕开放而遭致自己种族、文化的灭绝和既得利益的丧失。例如西汉时期的且兰君,因“恐远行,旁国掳其老弱”,缺乏远见和胆识,想“深拒固闭”,采取关门主义的办法,不受“王化”,以阻止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融化,结果导致国灭及其文化的中断。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边缘文化主体缺乏一种一切能为我所涵化的雄心与气魄,缺乏一种化腐朽为神奇、敢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自信心。以诗歌创作为例,贵州边缘文化的地域环境,使贵州诗歌创作与全国诗歌创作发展拉开了极为复杂的距离。在现代文学的发生阶段,诗歌并没有充当急先锋,既没有出现白话新诗这样的形式变革,也没有体现时代精神的诗歌运动,整个发生阶段所见都是一些古体诗,尽管内容上也能呼应主潮,但贵州由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经历了缓慢的历程,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以蹇先艾为代表的新诗人,才诞生了有规范意义的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