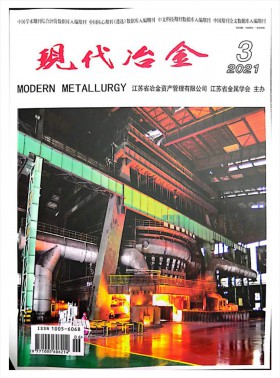一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中国现代文学“古典主义”倾向的问题偶尔有人提及,却难以见到深入具体的论析。近年来,相关论文和著作大量出现。总的说来,这些著述不乏创见,但不少论文中,“现代性”等理论话语的强行介入,大同小异的从学衡派到新月派再到京派的梳理,以及宣称发现了现代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匆匆忙忙的论断,并未切合作家和作品的实际。毕竟,名词概念的密集堆叠和逻辑的自我空转,最终无法取代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要给古典主义这一概念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固然是一场理智的冒险。然而,当人们试图用“古典主义思潮”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学衡派、新月派、京派、现代诗派乃至左翼文学一网打尽时,我们就有必要细究这一概念的内涵及背景,认真考察它对纳入其名下的对象的规约了。
古典主义是西方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17世纪出现于法国,后成为欧洲各国文学的楷模,对整个欧洲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18世纪末期的德国文学,都是典型的古典主义文学。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在封建王权的支持和鼓励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特征从思想上说,首先是受到王权的直接干预,主张国家统一,歌颂英明君主,文学和政治紧密结合。古典主义作品突出家族责任和国家义务,表现感情服从责任,个人服从义务的主题。其次,古典主义主张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之间的矛盾。最后,古典主义文学多以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为题材,继承古希腊悲剧的传统,描写宫廷和贵族的生活。其特征从艺术上讲,第一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吸取艺术形式和题材;第二是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如戏剧创作必须遵守“三一律”;第三是人物塑造类型化,人物形象性格单一;第四是追求庄重典雅的风格,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1]去除某些特殊因素,从普泛一些的意义上讲,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不同于作为一种美学倾向的古典主义,前者的内涵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二)崇尚理性;(三)强调规则与模仿。其中,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应为古典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古典主义思潮只有在政治的庇佑和监视之下,才能找到其寄身的确切位置。它浑身涂抹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散发出浓烈的意识形态气息。“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2]这种对秩序的悉心维护,往往与国家利益、政治利益直接勾连,不少作品甚至直接歌颂君主和王权,成为不折不扣的权力体制的附庸。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衡派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之上“昌明国粹”,与林琴南们之出于卫道的热情而攻击新文学有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学衡派并不具有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意味。这一点,与学衡派同时代的周作人看得十分明白,“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3]学衡派的文学观念代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期中的一种平和、稳健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抉择,它并未栖息于国家政权的巨大身影之下。因此,在与政治的关系上,学衡派与古典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而被许多论者视为现代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之枢纽的新月派,实际上却由一批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前期多持纯粹艺术的立场,后期虽涉足当时的文艺思潮论争,却强调文学家必须坚持人格的自由。即使是被认为最具古典主义特征的梁实秋,也拒绝依附于政治、权威。他认为“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约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所以,它要求“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4]京派作家更是力图超越急功近利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文学选择,疏远于国家意识形态,从容高蹈,专注于“纯正”的文学趣味,默默地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可以说,无论是学衡派、新月派,还是京派,都少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和为政治服务的意图,都没有直接依托于政权。正因为这样,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与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这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隙。
二茅盾认为,“古典主义只是理智的文学,没有热烈的情绪,不许奔放的想象,并且只是贵族的娱乐,描写着贵族的文学”。[5]这道出了古典主义独尊理性的特征。古典主义思潮推崇理性,其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惟理主义。笛卡尔将理性视为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照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心智活动,也应当受到这种理性原则的无情宰制。因此,感觉和想象力被视为杂乱的、变幻的、足以使人类精神活动招致欺骗的根源而遭到敌视和排斥。这种惟理主义乃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知识依据,诚如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所说的那样,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理性”拒斥感觉和想象,同时又表现出群体理性、政治理性的特征,显露出清晰的意识形态的专制面孔。学衡派之重视“理性”跟惟理主义观念很不一样。
以吴宓为例,他毕生追求“真情”与“至理”的统一,而对安诺德“诗专重理智思想而不及情感”的看法不以为然。他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古学派(一译古典派)之伦理的主张,乃一各种性行元素之调和融洽……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之上品,如荷马之诗,苏封克里之悲剧,以及桓吉尔(Virgil)之诗,其描写感情想象非不强烈,岂仅专重理性者。……后来之新古学派及伪古学派,特重一偏之理性,致由浪漫派之反动,专务提倡感情及想象。写实派继浪漫派而兴,复趋他一端,专主以冷静之头脑,观察社会人生之实况,详加描写,不参己见,其所重者乃为科学之理性。”[6]吴宓称古典主义为“新古学派”和“伪古学派”,因为它“特重一偏之理性”,所以对之持否定的态度。(朱光潜也称这种惟理主义的、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为“假古典主义”,并视十六世纪意大利人维达(Vida)的《诗艺》、十七世纪法国人布瓦洛(Boileau)的《诗艺》、十八世纪英国人蒲柏(Pope)的《批评论》为“假古典主义”的三部法典”。[7])吴宓强调诗与文“各该表示思想及情感,兼有其二,不废其一”。[8]显然,在文学观上,吴宓是反对惟理主义观念的。新月派提倡的是理性节制情感,借用朱自清评价闻一多诗歌的话来说,就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即便是被有些论者称为古典主义理论家的梁实秋,也只是反对过分推崇情感,不赞成把情感直接当成文学本身。京派提倡“理性与情感”的协调,其“理性”并不排斥情感,不过是针对当时文坛上情胜于理的普遍状况,针对情感过分外露的感伤主义倾向,要求“和谐”与“恰当”,其着眼点在于“艺术的完整”。比较而言,在布瓦洛的理性原则的强力框范之下,古典主义作品通常讲述的,乃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对情欲的最终克服,而非理性情欲终归要让人身败名裂,这无疑是一种理性专制主义姿态;而京派批评家所要求的,却是对赤裸裸的情感宣泄的适当“节制”,是“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9]沈从文、李长之、朱光潜、萧乾、李健吾、废名、叶公超、常风等人,均反对文学创作中过分的“热情”,而不排斥感情。至于京派开创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的事实,则早已广为人知。西南联大诗人穆旦、冯至、袁可嘉、李广田等的反“感伤论”,也和京派的主张相类。如果把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这种“理性”不加区别地简单等同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古典主义思潮所推崇的“理性主义”,甚至习惯于拿中国文学史机械地比附西方文学史,就很可能要冒牺牲中国现代文学史自身真实性的危险。西方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者坚信,合乎理性原则的伟大作品早已在古代诞生。拉布吕耶尔曾一口咬定: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p#分页标题#e#
在古典主义者那里,文学典范早已存在,艺术的全部规则都已为前人创制,后世文学须服从权威,匍匐在在经典的律条下反复揣摩、不断仿写。“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10]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学衡派,还是新月派,都没有掉入这种僵硬的泥古窠臼,京派更是以独具魅力的文学创作实绩,为中国文学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新质。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古典”的赞赏,更多的是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把从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作为创造的基础,而不是拜倒在某些典范和类型的脚下。例如沈从文,废名等作家,在文体上多有实验和创造,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史常识了。新月派关注诗的形式,因而屡遭“形式主义”之讥。闻一多的“带着脚镣跳舞”,是对“艺术自律”的强调,也是对新文学初期的白话诗以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趋势的反拨。当时许多新诗作品粗制滥造,让人生厌,新月派提倡创造诗歌的新格律,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了新诗本身存在的弊端。这种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目的是力图在传统诗词的形式彻底破坏、无形式成为了诗歌的唯一形式之后,探索和建构新诗的形式美。闻一多反对在创作上的任意而为,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方面多有创造性的建树。他提出的诗歌“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就是对诗歌语言形式的具体要求。新月派的诗歌格律运动与其说是古典主义式的模拟经典,不如说是恰当地运用传统资源的一种创新。从题材方面来说,古典主义钟情于反映上层社会的生活,不屑于描写下层社会的生活,具有鲜明的贵族化色彩。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以见到。京派与此迥乎不同,甚至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眼光注视着“乡下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有所贴近,文学视野较为开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刻画出了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其题材多取自下层民众的生活,体现出对小人物的关怀,而上流社会的教授、绅士倒成了被讽刺嘲弄的对象。
要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看不到对具体的经典的推崇与模拟,现代作家中,也没有人在主观上企图或在客观上做到了确立文学创作的规则与律条。不消说,就像许多论者详加梳理过的那样,学衡派、新月派、京派与“古典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间接的关联,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之处除了与古典主义的内涵之间的裂缝难以弥合之外,而且无论从理论构建、规模,还是从作品来看,它都无法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
首先,它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便是被一些论者认定为古典主义理论家的梁实秋,实际上也是受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文艺批评论》、《偏见集》等著作,虽然表现出与古典主义的种种联系,但大体上是坚持从文艺本身出发、从创作的规律出发谈创作,毕竟没有照搬或创制一套完整的“古典主义”理论。不能用梁实秋的理论表白来代替其创作实践,更不能用苍白的逻辑推理代替对其文本的细致分析。更何况任何文艺思潮都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边界,就算是有了思想家、理论家的某些思想言论,也并不意味着就有了文艺思潮本身。
其次,文艺思潮应该是有一定规模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结合的文学运动,而在现代中国,并无规模较大的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以新月派为例,它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团体,无非是一帮自由知识分子自愿地处在一起,“既无思想纲领,也没有奋斗目标”,“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凭着兴趣写点文章,谈笑作乐而已”,但是在“现代性”之类的知识框架下,有论者把新月派视为其成员之间有着高度一致性的现代中国的古典主义大本营,而“实际上,他们的情况远不像我们从前所估计的那样奥妙复杂”。[11]将学衡派、新月派、京派捆绑为一脉相承的集团,则显得更为勉强。
最后,然而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目前所见到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著述,大都不能从学衡派、新月派、京派的作品分析出发,去说明相关问题,去作出新的阐释,甚至不能明确地列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古典主义”作品。远离作品而得出的相关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三现代中国虽未出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古典主义一词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了描述功能。我们可用广义的古典主义或“古典主义倾向”来概括中国现代文学中某种家族相似性———一种重视传统的文化理念与和谐、静穆、均衡、节制的艺术风貌。吴宓、朱光潜所说的“古典”、“古典主义”,其实正是这里所界定的美学风格上的“古典主义倾向”。在《什么是古典主义》一文中,朱光潜所探讨的“古典的”及“古典主义”,即为“古典主义倾向”,而非“古典主义思潮”。[12]从梁实秋本人对“古典”的理解来看,他也并没有把“古典”和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混为一谈,其“古典”意指在立足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梁实秋指出:“‘古典的’与‘浪漫的’两个名辞不过是标明文学里最根本的两种质地。这两种不同的质地可以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土同一作家甚至同一作品里同时存在。”[13]他不把“浪漫的”与“古典的”理解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他所反对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滥情的极端浪漫主义。
1924年,本来信奉极端浪漫主义的梁实秋,在听了白璧德的课后,感慨良多,深为折服。他“开始自觉浅陋”,“对于整个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像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14]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本人并没有认为自己从浪漫主义转到了古典主义,而是受到古典主义的启发,从极端浪漫主义中走出来了而已。新月派的古典主义倾向表现为重视艺术规则,追求均衡、和谐的审美理想;既视情感为艺术的生命,又反对毫无节制的滥情。京派的古典主义倾向则表现为和谐、平静、准乎自然的审美风貌,浸润着东方式的静穆的艺术神韵。现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古典主义倾向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首先,20世纪初,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急剧膨胀,物质功利与人文精神的矛盾日趋激化。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吴宓、陈寅恪、梁实秋等,开始认识到物质主义的滋长,可致“人欲横流、道义沦丧”。[15]而新人文主义力图复活古典人文精神以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之弊,主张以道德理性节制情感,提倡和谐、均衡的美学原则,这就无疑成为学衡派、梁实秋之信服新人文主义的重要原因。其次,随着新文学本身的发展,一些人开始反思新文学运动的得失,要求吸取中国传统文学的养分,重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复次,政治局势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也使得不少作家向往稳定、渴盼安宁,因而把传统当作了精神的栖居地和心灵的避风港。最后,当浪漫主义的发展已到滥情与颓废的境地,艺术本身的品位已令人不满,那么,古典主义倾向作为对极端浪漫的一种制衡,其出现就是势所必然的了。#p#分页标题#e#
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具有的那种节制、均衡、静穆、和谐的美学风貌,诸如京派的小说和新月派的诗歌,与其说是新人文主义的中国版本,还不如说是在特殊的文化转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审美理想在现代文学领域中的承继、发扬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倾向,其实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种重视传统文化、具有传统色彩的文学理念和文学作品。使用“古典主义倾向”一词,不仅可避免使用“古典主义”这一概念时容易造成的误解,同时也更准确,更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真实。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照顾到了其所属“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纳入这一“倾向”的,除人们谈得较多的学衡派、新月派、京派之外,还有其他的流派与作家。如30年代的“现代”诗派。“现代”诗派虽不甚关注“理性”和“规范”,但也要求区别于极端浪漫的“坦白奔放”,要求对情感适当节制,以达到情绪表达的蕴藉与深入。“现代”诗派以传统审美心理为本位,选择和接受西方的现代诗学,所以苏汶在《望舒草?序》中称戴望舒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就拿这几个文学流派来说,他们各有自家的特点,甚至即使同一个流派里,不同的作家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学衡派和新月派对传统文化的择取,主要偏向于儒家,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如梁实秋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就十分欣赏,他认为儒家思想接近西洋的人本主义(即新人文主义),孔子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颇多暗合之处,于是择取人本主义的文学观。而京派与道家文化有着更深的亲缘关系。有趣的是,梁实秋和闻一多虽私交甚深,在文艺理论上也确有相似的倾向,但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混为一谈。例如,梁实秋依白璧德的说法,认为在中国,道家的文学思想很像是西洋文学中最趋极端的浪漫主义,因此,他对老庄思想持严正的批评态度。闻一多却对道家、庄子颇有好感。
1929年,他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庄子》,欣赏庄子的超然物外、终身不仕,他以庄子为“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梁实秋稍显拘谨、保守与清高,而闻一多却是浪漫的楚人,其一生充满激情。他曾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到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16]又如京派作家(比如废名)无论是其人还是其文,大都呈现出一种“静”的风格,而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却颇有活泼泼的“动”的特点。就算是徐志摩跟闻一多,也有较大的区别,后者又更加强调情感的力度。不难看出,如果一味“求同”而不“辨异”,给他们贴上统一的古典主义标签,就难以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聚讼纷纭的两个概念。对于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艾布拉姆斯说:“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7]以此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倾向,去考量具有这种倾向的新月派、京派,就会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来的心灵对世界的投射、充沛的想象力、理想主义笔触、对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视等等,都足以说明它们不再属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范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倾向是对极端浪漫趋势的制衡,是对“伪浪漫主义者”的批判。古典主义倾向与浪漫主义并非不共戴天,它本身就是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就新月派和京派而言,古典主义倾向与浪漫主义思潮并无根本的抵牾,正如李健吾对萧乾的评价:“在气质上,犹如我们所分析,他属于浪漫主义,但是他知道怎样压抑情感,从底里化进造型的语言,揉合出他丰富的感觉性的文字。”[18]这里,李健吾的论断如果换一种更简洁的表述,即萧乾可归入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一类。与此相似,由于较为重视情感(或美学),朱光潜认为古典主义(倾向)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部分:“佩特(WalterPater)说浪漫运动是浮士德和海伦的结婚,浮士德是中世纪幻想和热情的结晶,海伦是希腊美的代表,可见古典主义也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成分。”[19]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和京派所表现出来的古典主义倾向,就糅合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难以从浪漫运动中剥离出来。有研究者曾指出,新月派是具有某些古典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团体;而京派也呈现出与五四时期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暴躁凌厉、悲怀伤感的风格不同的特点,他们是“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的浪漫主义”。[20]可见,本文所探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倾向以及这种文学精神的主要承载者新月派和京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悖离浪漫主义,而是构成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特殊表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与运动的独特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