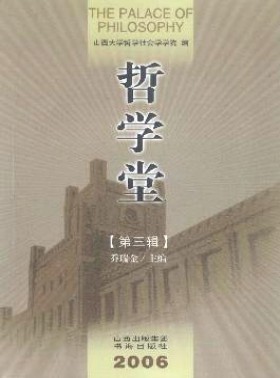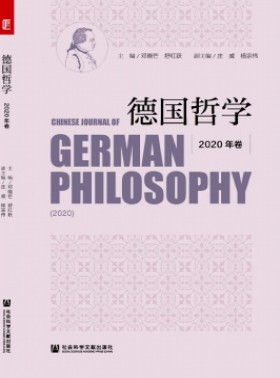一、哲学美学和文本使用、效果说 20世纪中后期,后解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的主张,冲击着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个“消解的时代”,西马必须在内部重新批判性反思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中,人们也重新审视“文学”及其本质问题,“文学是什么”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贝内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传统极为不满,他惊异地发现人们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哲学美学,用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甚至早期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置换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论证立场完全背离,是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 为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赋予审美的先验地位,清除马克思美学中残余的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即后康德主义,贝内特重新审视“什么是文学”本体论问题,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在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形成有效对话。贝内特指出形式主义的贡献是他们从文学与非文学关系性构成看待“文学性”,在“文本使用”的功能中界定“文学性”(陌生化),不但推翻了现实主义模仿论,而且也道出传统文学本质论的荒谬。通过形式主义的启示,贝内特指出文学并无本质,有的只是文学在一定系统中的位置和相应的功能,而功能变化则依据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文本使用来决定。贝内特通过符号差异系统的“功能说”说明了“文学性”仅是文本社会性使用的结果,就此打破了阿尔都塞学派审美、科学、意识形态三元对立的先验性,以恢复“文学性”的唯物化、历史化维度。同时,他又不满卢卡奇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将“文学”的历史规定性还原为经济基础和普遍的历史规律上,这种从文本的符号所指系统中间接获得的文本“社会效果”根本无助于说明文学鲜明的历史性、具体性,它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抽象唯心论和经济化约论。贝内特认为只有从文本的社会性使用和使用产生的社会效果(包括政治效果)中才能历史而具体地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没有独立存在的作品和文本,它们必须置入具体的使用中才能显示自身,这是文学批评所要分析的重点。”[1]当贝内特将文学重心位移到文学的社会性使用,从文本使用中洞察文学的社会效果时,便已体现出贝内特的社会学功能主义立场的实用主义倾向。他试图从文学消费接受角度探寻一条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路径,将“文学”“审美”彻底唯物化、历史化。但是,“文学的社会性使用及其效果”究竟是怎样的,其具体机制如何?贝内特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说明。 二、阅读形构/互-文性 80年代中后期,贝内特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文学的社会性使用及其效果”的具体机制。 首先,他提出“阅读形构”概念。阅读形构指特定的力量形塑、构成、铭刻于文本和读者中,具体而言,指涉特定语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互-文关系。 在其中,文本和阅读为彼此而存在,且文本总是已经被文化激活的对象,读者总是被文化激活的主体”[2]。它有以下几个内涵:(1)阅读形构是物质的、历史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等各种后天社会文化压力形塑的阅读前见。它们以一系列话语形式和互文力量施于读者阅读过程。(2)阅读形构发生在阅读接受过程中,是同一文本以及各种不同话语在同一读者或不同读者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文本、文本与文本的动态交叉网络关系。故称为“互-文性”。(3)文本在阅读中,被不同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铭刻而进行无穷无尽的重构和转变,并被不同方式被文化地激活,故文本是阅读主体互联的文本组,是“为读者的文本”。(4)主体是被文本意识形态不断质询和重构的过程,其身份不断被瓦解,进而修正原有的阅读形构,主体是“为文本的读者”。其次,贝内特将文本效果界定为围绕文本历史性接受而产生的多元甚至矛盾的效果场域。“文本本身没有效果,只是生产效果的场所,那么效果显然就是一个实践问题,亦即如何以最佳方式介入文本效果的生产过程。”[3] 这就意味着文本自身不存在先验的效果,包括文本的真理认识效果,效果是介入性的生产过程的结果,政治性介入尤为如此。这就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试图透过文本洞察真理的文学认识论。这是贝内特在吸收福柯与墨菲和拉克劳等人话语理论基础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本认识论的解构,倡导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政治介入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既然真理是话语建构的结果,那么对真理的建构、利用以及效果,比真理本身更重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前政治任务就是在与资产阶级霸权斗争中,政治性地积极建构真理话语框架,进而组构历史行动者的意识和实践,争得意识形态霸权。 贝内特为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审美自律性,从“什么是文学”入手,得出文学性是“文本的社会性使用和效果、功能”的结论,并将后者理论化为“阅读形构/互-文性”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阐明仅仅涉及到个体具体的社会解码行为,不能真正说明制约“文学”功能发生变化的社会历史机制,后者是社会文化编码行为。为此,贝内特继续思考制约“文本的社会使用”发生和变化的历史机制问题,并在文本的社会使用制度中获得了答案。 三、“文学”是制度性话语空间 90年代,贝内特对文学(审美)他律性问题思考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制度角度思考“文学”本体论,此时,贝内特理论基础转向了福柯。同以往一样,贝内特依然批判传统西马哲学美学,但其立场已不是早期从局部修正传统西马文学唯心成分,而是从本体层面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超结构的经济化约论的本质主义倾向,进而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的束缚,重新建构一种“文学形式、功能和效果的历史社会学”即新型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文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要点:首先,消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贝内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联接理论是对西马理论中作为饱和的、自我定义的总体性的“社会”的消解,贝内特肯定这一立场有利于重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铸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先验性,它既阻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难以真正历史化,也妨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介入。贝内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表征认识论造成历史是文本的最终指涉的文学认识论,而事实上,历史也和文学一样是话语建构的制度性话语表征空间,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并不包含如何接近历史的一般认识论问题。#p#分页标题#e# 其次,对“文学”的界定。贝内特从具体分析文类这一文学内部制度入手阐明更具历史具体性、偶发性的文学观。文学不是以本质主义和普遍历史规律为基点的文化逻辑,但也绝不意味着像解构主义永远无限延义的语言嬉戏,它是为社会化、历史化的特定制度所制约的话语的具体社会使用和偶发性的效果场域。它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领域和构成性部分,因为文本的社会使用和效果直接建构了阅读实践,并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是一种具有现实直接性的自我技术即审美治理性。贝内特就此重新界定文学本体论空间“文学是社会组构的表征空间,其独特处在于制度地、话语地对所选定的文本的使用和部署”[4]。 再次,阐明制约文学话语的使用和效果的具体制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审美是自我技术。意即调解和控制文本的社会性部署和使用的社会性编码行为或者说制度是“治理性”。换言之,文学的使用和功能、效果与社会管理机制息息相关,它们作为文化资源,为特定的辖治规划裁定,并产生相应的效果,最终影响个体的自我行为。 最后,贝内特的立场始终是后现代的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即在对某一历史条件中的社会现象分析时,强调多元历史条件和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偶然性机制。故文学分析的焦点是差异化、具体化的密度历史,理解相互作用的条件复杂性和产生的弥散性效果。 贝内特将文学看做在文本使用和效果中与其他社会领域互动交叉的动态性网络场域时,意味着他的视角已经超越了文学领域,而对“文学制度”问题的进一步思索,也需在“文学之外”才能真正落实。贝内特90年代后转向文化研究,这是他解决“文学他律性”问题的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