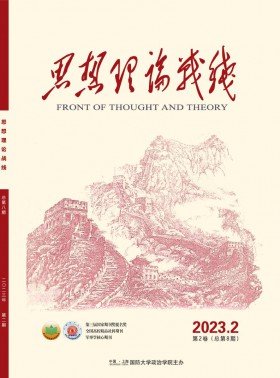作者:李晓梅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1938年10月15日,一代曲学大师吴梅躺在病榻上写信给自己的弟子托付后事。这位弟子不负厚望,在吴梅去世后,在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刊行了老师的三部遗作,使之得以面世。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受到吴梅器重的弟子却由于种种原因,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失踪者。这个人就是曾被称为“江南才子”的卢前。卢前的一生,是颇为坎坷的一生。他出身于书香故家,却在大学期间就为经济所迫,兼职奔波;他才思敏捷、才华横溢,却又经历动荡的时局,四处漂泊;他一心救国,却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备受冷遇;他热爱教育事业,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被迫离开深爱的岗位。卢前家学深厚,饱读诗书,笔下洋溢着浓郁的书生才气,和吴门其他弟子一样,卢前也是在新的教育和学术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学者,接受新式教育的他能够自觉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补充自己。在研究中他自觉运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研究的科学化、体系化,因而取得了许多的实绩,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卢前的文学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卢前文史论稿》和《卢前笔记杂钞》中。深入地思考和不断地实践,促成了卢前文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在《四知》一文中,卢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优熟劣、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的发展是进化还是退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哪一种更适合新时期文学的需要以及如何对待古今文学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的现代因素。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广大国民思想意识的更新对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于是他们发动了晚清思想启蒙运动和晚清文学改良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向广大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掀起了后来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1917年,《新青年》又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举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大旗。“八不主义”和“三大主义”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傅斯年、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积极响应。钱玄同视摹仿六朝骈文的文选派文人和摹仿唐宋的桐城派文人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1]。胡适也一鼓作气提出文言已经是死掉了的语言文字,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2]。周作人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都有许多“非人的文学”。虽然进入二十年代中后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思了自己过激的主张,但在当时,这些主张确实对广大的青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众多高等学府,青年们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却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现象较为普遍。卢前曾创作过一首小令[一半儿]“:拜伦、戈德果如何?诗国新开碧眼科。李、杜、苏、黄未必多,你知么?一半儿‘焉斯’一半儿‘努’。”表现了对广泛存在于青年中的重“西”轻“中”思想的担忧。
的确,“五四”以后,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纷纭呈现,而又层层高盈,生活在这个由新概念、新名词所编织而成的政治文化之下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行动的方向都发生了变化。年轻的读书人可能因为对旧的已经失去信心,对新的未知的世界又无限向往,因而一两个名词或一两个概念,便可能成为一种形塑个人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卢前非常认同吴芳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同时他接受了黑格尔对文学民族性的阐释:“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的观念的目的”[3]认为民族性是一种文化的根基。卢前认为中国要建立新文学,使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国知识分子应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做到“不忘其本”。他说:“文生于情,情因国性。以温柔敦厚为诗教者,中国文学之精神也。吾人生于域内,禀受如是。舍己从人,不可也。今欲跻中国文学于世界文坛,正应发展固有,以有别于他而自立,庶无削足适屦之弊。”在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卢前主张积极有效地利用西方文化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适时的补充。他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新的历史时期所暴露出的诸多不足,因此他期望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时,更加注重西方科学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在讲究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学术大势中,建立新文学,实现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卢前这种“不忘其本”的主张,乍一看似与复古派属同一论调、仿佛与“五四”精神有所背离,但认真思考后不难发现,卢前是站在“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立场上提出“不忘其本”的,与胡适等人的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不同的只是,他为纳新加入了一定的条件,所以其本质与“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二、《四知》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文体递变,代有偏胜。固有体裁,未尝废焉。词盛于宋,苏黄二陈之诗,卓然不朽。曲创于元,姚卢虞刘之文,并有足多。不可以其词而弃其诗也,不可以其曲而弃其文也。文章一体,必适宜表见其一种之情。人各不同,体各有别。以曲为词,未免直率。以文为诗,风神顿减。文体固不可相假也。且新出于旧,岂可泥旧而鄙新。旧亦尝新,岂可泥新而鄙旧。”这是卢前针对当时学术界出现的文学激进派和文学保守派的激烈论争发表的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两种主张都有偏颇之处:激进派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希望在割断文学民族性的情况下,借助西方文化建立中国的新文学,这种移植是不科学的;同时,保守派一味驻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忽视了文学的时代性特征,反对文学与时俱进,也会丧失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和互补的有利机会。卢前用一种相对客观的现代意识和思维方式肯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首先,他引用日本帝国大学校长井上哲次郎的话论证了“中国文学史壮矣”:“支那、希腊、罗马、希伯来、珊悉讫利多(印度也)诸文学,皆有千古不磨之价值。犹太在西洋式微极矣,其遗民几受非人之待遇;然而希伯来文学之研究,尚不能预测其告终之时机。惟支那文学,尚在西洋人未甚研究之域,除《诗经》已译外,李青莲、白乐天、苏东坡之诗,亦稍稍为彼译出。顾上下三千年之文学,以历史眼光考察之,岂彼等所易企及之哉。”[4]进一步,他认为文学活动具有历史继承性,“盖今人之性情习惯,皆得之古人,黄白面貌虽不同,然皆具人类之共性。精神上相契合,有历史性与群众性,是以文化得以继续不绝,可期大同。”这种历史继承性不仅表现在优秀文学传统直接影响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方式方面,还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上。的确,纵观中国文学史,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几乎都经过了由简到繁、由粗朴到精致、由不够完美到逐渐完美的过程。这是一个前后不断继承发展的过程。每个时代出现的文学繁荣,都是以前代文学发展为重要前提的。因此卢前希望现代知识分子能够抛弃“西方文化中心论”论调,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设置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中加以考察,从而探询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由此可见,卢前的文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始终把握在中西融合中的现代化转换方向的。#p#分页标题#e#
三、王国维1905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指出:“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5]。的确,进化论思想的传入,对于中国当时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梁启超、刘师培、胡适等人都曾运用进化论来论述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轨迹。胡适曾在日记中写到“: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6]胡适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胡适的所谓“革命”其实就是进化。胡适进一步这样解释说“: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7]。胡适正是以进化论作为文学革命的理论根基,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纵观西方文化史,与文学进化论相对地,西方文化中还存在“文学退化”的观点,如未来派、达达派就坚守这样的立场。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无论是文学进化论还是文学退化论,卢前都不予赞同。首先,就胡适等人提出的文学的五期分法,每期都是前一期进化的结果的观点,他指出:“……五期者,皆自简单进而为复杂,自少数进而为多数。第一期,以声音动作表现情绪。第二期,具言语文字乐调。第三期,更进而有抒情记事之诗,历史哲学之文。第四期,则贵族之特殊文学。第五期,则为平民之一般文学。其说如此,意有未尽者,盖自其纵而观之,自原素萌芽期,进而至成立期,非进化现象,乃自然之理。自专有期进而至普遍期,亦非进化现象。依彼所眼所言,然则专有期之前,文学岂不普遍乎?且普遍期中,仍有贵族平民之别,至近代始有劳动阶级文学家出现。此乃时代使然,不得谓之进化也。”卢前从时代、逻辑等方面否定了文学进化的观点。同时,他指出:“然时代之精神变化不息……是个人有个人之文学,各时代有各时代之文学,故时代之转易,文学亦随之转易,若生物之变化然。”否定了文学退化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卢前从“一切事物,因果环生”的哲学角度提出了文学“蜕化”的观点:“古今文学,一部分进,一部分退,进退互有其理。盖文学之演进,若蝉之蜕皮,若蚕之破茧,层出无穷,谓为有优有劣、有进有退可,谓为无优无劣、无进无退亦可。此不独文学为然,一切事物,因果环生,莫不如此。进化退化,何必轩轾其间!无已,名之曰蜕化可耳。”
在进化论被普遍承认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前提出“文学蜕化”这个观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暂且不论“蜕化论”正确与否,无可否认,进化论在五四时期的语境之中是一个强大的知识背景,大有成为“公理”的趋势。卢前能够不人云亦云,在激进的时代风潮中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性进行科学的怀疑和批判是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成熟的一种体现;其次,文学进化论的理论根基———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弱点,近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质疑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再次,卢前的文学“蜕化论”的提出,有利于纠正存在于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用进化论观点进行文学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较为盛行,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强调过多,使得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这都无利于建立文学史的民族品格。虽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明确对进化论提出了质疑,如周作人在1932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相对卢前的自觉,已是晚了一些时候了。
四、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五四时期如火如荼的紧张气氛感到惊异。学者余英时曾经用“激进”与“保守”的对抗模式分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提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8]的观点。的确,激进情绪是五四时期一注潜在的涌流。尽管激进情绪未曾出示几条固定的口号纲领,但它却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无意识,暗中左右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发言。胡适在倡导新文学之初就明确提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文学”[9]。陈独秀更是主张新文学必须“赤裸裸的抒情写世”[10],认为“抒情”与“写世”应该是文学不可分割的职能,并且呼吁把建立“写实文学”标上文学革命的大旗。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理论运作,“现实主义”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重要概念,具有了异常的号召力乃至威慑力。许多作家自愿地割弃既有的文学主张,归依于现实主义的麾下。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已经明确地摆出了决裂的姿态,批评家不愿在理论上过多地垂询传统文化,所以他们过度地扩大了“写实”的意义。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的创作,作家话语主体背后的个性、风格、性情、格调、感伤、感觉等概念会被淡化,作家的想象力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现实主义”这个涵义不明的外来术语,卢前进行了潜心研究。在考证了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产生过程后,卢前认为现实主义是世界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文学家安慰人生的一种做法。这个主张将现实主义由所谓的一种进步文化、正确世界观和先进阶级的标记又还原为一种文学类型,使之真正与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独立开来。其次,卢前认为对现实主义中的“真实”应该具有较为科学的认识。
他以莫伯桑为例,指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以“历史理性”求“真”,在创作中区别生活的真实和科学的真实,建立起艺术的真实,要求作家以假定情境表现自己对社会生活内蕴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感悟,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卢前着重指出,提倡现实主义不应该与中国古典文学完全决裂,因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现代的文学家应该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现实主义,以求在高涨的文学激情中理智地书写自己对社会的关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化变异较为明显的时期,研究这个时期学者的思想流变对我们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有一定帮助。作为这个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卢前文学思想中的现代因素是值得关注的。研究它们,会有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