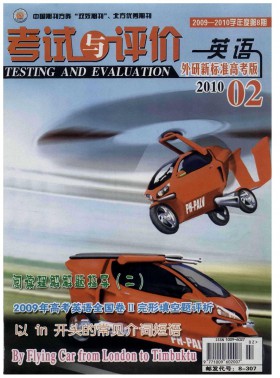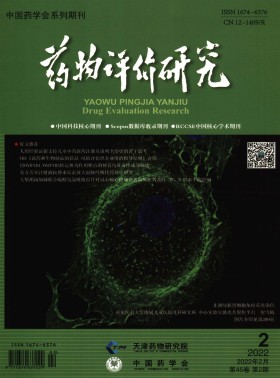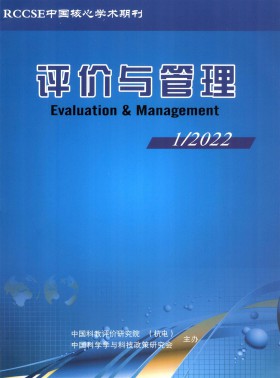作者:杨冬 王翠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北华大学外语学院
作为俄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维萨利昂•别林斯基(1811-1848)对俄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却长期在俄罗斯和中国学术界遭到了严重曲解。一方面,人们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与德国文学理论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肯定其后期思想进步意义的同时,却忽视了他早期批评中的许多重要见解。因此,重新认识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正确评价他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或许是对这位批评家最好的纪念。
一、在早期论文《文学的幻想》(1834)中,别林斯基通过对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历史回顾,反对盲目摹仿西欧文学,热切呼唤一种真正植根于俄罗斯生活的民族文学。为此,他从史雷格尔兄弟那里借取了一个重要观念,即把文学看成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别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文学是人们“在自己的优美的创作中充分地表现并复制着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共同过一种生活、共同作一种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把那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表现得无微不至,直触到最隐蔽的深处和脉搏”[1]10。文学的民族性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1]107。以这一标准来考察,别林斯基不禁深感失望,因为一部俄国文学史,“不过是通过盲目摹仿外国文学来创造自己的文学的这种失败尝试的历史而已”[1]110。甚至在普希金的创作中,真正体现民族精神的也只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因此,别林斯基热情期待着这样一天:“这一天总会来到,文明将以波涛汹涌之势泛滥俄国,民族的智能面貌将鲜明地凸现,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将在自己的作品上镌刻俄国精神的烙印”,“到了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文学,我们将不是欧洲人的摹仿者,而是他们的劲敌。”[1]124
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再次采纳了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文学分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两大类。他指出:“诗人或者根据全靠他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时代和民族的态度来决定的他那固有的理想,来再造生活;或者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1]147与此对应的,则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客观诗人和以席勒为代表的主观诗人之间的对比。在别林斯基看来,莎士比亚没有理想,没有同情,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那广无涯际的、包含万有的眼光,透入人类天性和真实生活的不可探究的圣殿。”[1]152而席勒的作品却是为了表现诗人的思想情绪而创作的,它“没有生活的真实,但却有感情的真实”[1]157。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往往将上述见解视为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石,但这一判断却是大可怀疑的。诚然,别林斯基在此多次使用了“现实的诗”、“生活的诗”等字眼,但我们却应当认识到,有关“理想的诗”与“现实的诗”、“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所作的区分,早在浪漫派批评家那里便已明确提出,何以一经别林斯基转述,就成了现实主义理论?何况除了俄国作家之外,别林斯基赞誉的是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拜伦、乔治•桑和詹姆斯•库柏等人,他们的创作与通常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也相去甚远,何以仅凭几个概念就断言别林斯基的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在此反复强调了文学创作的非目的性和非自觉性。在他看来,“创作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这便是它的基本法则。”[1]177具体地说,当诗人产生创作冲动,要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他是自觉的;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孕育中的作品就不再被诗人的意志所左右,因而,创作又是无目的和不自觉的。别林斯基甚至宣称:“诗人是他的对象的奴隶,因为不管是对象的抉择或是它的发展,他都无法过问,因为如果没有那绝对不依存于他的灵感,无论是命令、订货或是本人的意志都不能使他创作。”[1]180显然,这与他后期评论中坚持艺术必须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限于篇幅,我们无法逐一评述别林斯基的论著。不过,在他的早期批评中,还有三个理论问题应予以重视。这就是形象思维、典型化和有机整体论问题。虽然我们不难在德国批评家那里找到他们的理论渊源,但由于别林斯基对这些问题作了较多发挥,从而深刻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
如果说有关创作非自觉性的说法主要来自康德的话,那么,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理论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强调:“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索,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绝对真实,不过不是表现在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中,而是在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诗人用形象思维;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2]96然而,尽管形象思维的理论表明了别林斯基对艺术规律的探讨,但所引发的问题也是毋庸讳言的。首先,由于该理论把诗歌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导致文学研究忽略了作品文本而滑入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领域。其次,形象思维的说法过分看重视觉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却忽视了其他艺术技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视觉意象只是诗歌艺术中的各种技巧之一,并不比其他技巧更特殊、更有效。而这也正是后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所强调的。别林斯基也高度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把典型化视为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他指出:“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化……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个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1]191在此,别林斯基借鉴了黑格尔的见解,将典型看作是体现某种普遍概念的代表,认为典型化就“意味着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来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2]102。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典型应当是高度个性化的,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物。只有在这条件下,只有通过这些对立物的调和,他才能够是一个典型人物。”[2]25同样,有机整体论也是别林斯基早期评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他看来,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没有最好的场面,因为里面也没有最坏的场面,一切都是出色的,都是艺术地构成那统一整体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142他甚至借用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艺术作品比喻为植物的生长,“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2]251尽管这似乎是一种老生常谈,但别林斯基强调的却是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表明了他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直到后来,他才放弃了这一评价标准,代之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p#分页标题#e#
二、1841年,别林斯基雄心勃勃地计划撰写一部系统的诗学著作。从写作计划来看,此书规模相当庞大,意在“有系统地认识美学法则,以及以此为基础而有系统地认识祖国文学史”[3]2。但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并未完成,仅仅写出了四篇论文———《诗歌的分类和分科》、《艺术的概念》、《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和《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就完成的这些论文看,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并不多,许多见解仍然来自于德国文学理论。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贬低别林斯基,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不难发现,别林斯基的体裁理论基本上照搬了黑格尔的观点,只是在个别细节上作了若干修正。在他看来,诗歌可以分为叙事诗歌、抒情诗歌和戏剧诗歌三类。叙事诗歌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诗歌,宛如建筑、雕刻和绘画;抒情诗歌是主观的、内在的诗歌,可以比作音乐;而戏剧则是叙事的客观性和抒情的主观性的统一。别林斯基称颂歌德和席勒是“抒情诗歌的两个完整世界”,也赞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司各特和彭斯的创作,而法国却没有抒情诗,其水准绝不超出民间歌谣之上。就戏剧而言,首先是莎士比亚,其次是德国悲剧,法国戏剧则“属于服装、时装以及良好古老时代的风习的历史的范围,但却跟艺术史毫无任何共通之处。”[3]79由此可见,直至19世纪40年代初,摒弃新古典主义趣味,拥护浪漫主义文学,仍然是别林斯基批评活动的基本倾向。
《艺术的概念》一文开宗明义,对艺术作了如此界说:“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用形象思维。”[3]93关于形象思维,这里无须赘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这样两点:首先,别林斯基在此论述了黑格尔的哲学,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从宇宙到人类的精神,都看成是绝对理念的辩证的运动。而人类的精神发展则经历了从神话到艺术,最后到哲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次,所谓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其“直感”就意味着“存在以及毫无任何媒介而直接发于自身的行动”[3]103。别林斯基强调,“直感的”与“不自觉的”并非同一个意思,“现象的直感性是艺术的基本法则,确定不移到条件,赋予艺术崇高的、神秘的意义;可是,不自觉性不但不是艺术的必要的条件,并且是跟艺术敌对的、贬低艺术的”[3]107。这表明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已发生了变化,早期所推崇的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此时已遭到质疑。与此同时,别林斯基也强化了历史主义观念。他指出:“文学的意思是指历史地发展起来并反映出民族意识的文辞作品。”[3]117“发展的有机的连贯性,构成着文学的特点,这也就是文学之所以有别于文辞和文录的地方。”[3]120因此,不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学,就不可能理解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不了解17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也就不可能理解现今的法国文学。但与《文学的幻想》不同的是,别林斯基在此承认,俄国民族文学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它“从来不曾有过,并且现在也不可能有全世界历史性的意义”[3]155。
《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继续讨论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由于别林斯基此时已较娴熟地掌握了辩证法,因而他强调民族性只有与“一般人类事物”的共同性结合起来,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正如他所指出的:“人们在文学中仅仅要求写出‘民族性’,等于是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虚乌有’;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在文学中要求完全不写‘民族性’,认为这样可以使文学为所有的人所理解,成为普遍的东西,就是说,人类的东西,也等于是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虚乌有’……很显然,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3]186然而,贬低民间文学的观点却依然如故。因为,在别林斯基看来,民间诗歌产生于一个民族尚未自觉的婴儿时期,其内容只能为本民族所理解,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3]211。这当然是一种错误见解,在大量文学史事实面前将不攻自破。
三、大致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与前期推崇客观诗人而贬低主观诗人的立场不同,他转而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主观性,强调诗人的个性和激情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与前期崇尚艺术的自足性不同,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三,前期所持的有机整体论开始松动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并越来越多地从内容方面来看待文学作品的价值。当然,所有这些变化是与他整个世界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所知,别林斯基的早期评论是完全倾向于客观诗人这一边的。但在《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2)一文中,他却出人意外地把诗人的主观性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看来,果戈理迈出的重要一步,便是在《死魂灵》里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主观性。这当然不是指那种歪曲客观生活的主观性,而是强调作家在真实描写外部世界的同时,又注入了创作主体的强烈爱憎。正是这种主观性,“不许他以麻木的冷淡超脱于他所描写的世界之外,却迫使他通过自己泼辣的灵魂去引导外部世界的现象,再通过这一点,把泼辣的灵魂灌输到这些现象中”[3]414。因此,在别林斯基看来,《死魂灵》并不像那些御用文人所说的那样,是对俄国社会的丑化,而是对这个社会的丑恶现象的鞭挞,其中“洋溢着对俄国生活的丰饶种子的热情的、神经质的、带血丝的爱”。
在鸿篇巨制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中,别林斯基更把这种主观性称为“激情”,认为它是理解诗人个性和创作特点的关键。他指出:“每一部诗情作品都必须是激情的果实,必须被激情所渗透。没有激情,就不可能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迫使诗人执笔作文,给予他以力量,让他有可能写完一部篇幅浩繁的作品。”[4]336当然,艺术中的激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理智对意念的简单的理解转变为精气充沛的、强烈追求的对意念的爱”[4]335。就此而言,激情既是体现于作品中的统一的精神,也是创作活动本身的驱动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如果一个诗人决心从事创造活动,这就是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不可克服的热情推动他、驱策他去写作。这力量,这热情,就是激情。有了激情,诗人就爱上意念,像爱上一个美丽的、活生生的人一样,就热情如焚地被概念所渗透……”[4]334在早期批评论著中,别林斯基曾多次表述了有关艺术的自足性的思想。他声称:“诗人如果在作品中力图使你们从他的观点来看生活,那时他已经不再是诗人,却是一个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恶劣的、用意不良的、该诅咒的思想家,因为诗歌除了自身之外是没有目的的。”[1]24但在后期的批评活动中,别林斯基却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中强调:“我们的时代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赋予19世纪的艺术以历史倾向,这就意味着:天才地猜透了当代生活的秘密。”[3]584#p#分页标题#e#
不仅如此,随着民主意识的日益觉醒,他越来越坚决地主张艺术要为社会的崇高利益服务。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综述中,他在总结俄国“自然派”文学的发展历程的同时,更明确地宣称:“艺术本身的利益不能不让位于人类更重要的利益,艺术高贵地承担起为这些利益服务的担子,成为它们的发言人……从艺术手里夺走这种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这不是把艺术抬高,而是把它贬抑,这样就等于是剥夺它的最有生气的力量,也就是思想,使它成为某种放荡逸乐享受的对象,成为空闲无聊的懒鬼的玩具。”[5]597与此同时,别林斯基的批评思想也发生了若干变化。在早期论著中,他曾把法国的历史批评与德国的思辨批评对立起来,并认为前者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不承认美的规律和作品的艺术价值。因此,要评判一部作品的艺术性,就必须求助于德国的思辨批评[2]153。而在后期的评论中,别林斯基既然强调艺术是从属于社会历史进程的,那么,他就必然借重于历史的批评方法。他这样指出:“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对时代、对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对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对他的生活、性格以及其他等等的考察也常常可以用来解释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忽略掉艺术的美学需要本身。”这就是说,文学批评应做到历史研究与审美评价的统一,“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3]595。因此,这一批评思想已达到了很高的认识水准。不仅如此,别林斯基也越来越深信,艺术才能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它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作家的成就和整个文学的发展也完全是由时代精神决定的。他断言:“诗人同他那个时代的关系往往是双重的:他或者是在那个时代范围内不能为自己的才能找到非常重要的内容,或者是不遵循现代的精神,因而不能利用时代为他的才能所能够提供的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才能的过早衰落和正当获得的荣誉的过早损伤。”[3]525
类似见解也贯穿于《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中,以致他确信,要评价普希金这样一位天才诗人,“不可能在纯理性的基础上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不,它的解决必须是社会的历史运动的结果。现象越是崇高,就越是富有生命力,而越是富有生命力,就越是必须依赖于对生活本身的运动及其发展的自觉”[4]6。但这样一来,别林斯基最终就走向了所谓“时代精神决定论”。这就是说,无论一个作家成功与否,他的创作均可以被归结为时代的运动,仿佛一切都是由历史所决定的,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审美的评价。在后期评论中,别林斯基也对同时代作家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作出了及时反应。然而,他却未能坚持有机整体论的诗学标准,更多地是从思想倾向上来考察和评价作品的。他要求俄国文学在农奴解放运动中起到促进作用,“文学本身不仅反映了这种倾向,还要促使这种倾向在社会中的成长,不仅是不落后于它,还要更加超越它”。当然,“艺术首先应当是艺术,然后才可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5]586。也正是后期批评中的这些激进思想,把别林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烈夫等人的批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