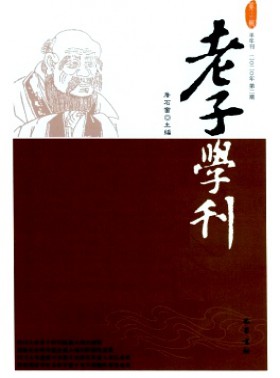作者:1元永浩 2金月善 单位:吉林大学 “有”与“无” “有”字在现代汉语中是个最抽象的词,它表达事物存在着的状态,或指事物表象的持存状况,或指性质的确定状态。不过,在古人那里“有”字的含义并不如此抽象,在甲骨文中写成“又()”,象“右手之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有”字最初象征右手,而后来却演变成表达存在的抽象词汇。那么,此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显然,人的手具有把握、把持、控制或驾驭的功能,而这些行为的对象是感性事物。反过来说,只有那些具有感性确定性的事物才能被人的手所把握、把持、控制或驾驭。也就是说,凡是人的手所把握的对象都具有感性确定性。那么,我们是如何确定一个具体东西的存在呢?中国自古有“眼见为实”的说法,认为视觉是一切确定性的最牢靠的基础。不过实际上,视觉对感性事物的确认还不是十分牢靠的,因为视觉还会存在一些幻觉或错觉。最可靠的感性确定性来自于触觉的确认,因为触摸到或把握到的东西肯定是实存的。 当人们把“有”字写成“又”的时候,这个字所强调的是手,而不是手所把握的对象。于是后来在又字下面加上肉字的有()来表达“以手持肉”时,该字所象征的东西从手转移到了手所把握的对象。“以手持肉”本来意味着富余,故后来引申为“五谷丰收”。如《谷梁传•桓公三年》中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4]444在古人那里有肉有谷物就意味着拥有一切无所不有,于是“有”字开始抽象化而获得形而上的意义。如此说来,中国古人的存在意识根源于生存的谋划,因而认识事物也被理解为以思维来“把握”对象的行为。古人总是愿意用“万物”一词来指称天地间所有的事物,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大体上可分为一万种。显然,“万物”这一命名已经属于人对对象世界的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是一种目的性行为:首先人们把这些事物当做自己的对象,然后通过命名、规范等方式对事物进行排序,再然后用这些事物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这里人们之所以能够把握对象是因为,那些被把握的对象给人们提供“把柄”,而这个“把柄”就是事物的确定的表象或稳定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事物的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本质才能把持这个生活的世界,这稳定的本质和确定的表象恰恰构成事物存有的内在根据。 然而人的生活的经验说明,人们手头上的所有的事物没有一个是永恒的,曾经拥有过的美食、金钱、荣誉、权利都终将化为乌有。此所谓,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所谓的变化也就意味着,“有”与“无”之间的相互转化。那么该如何理解“无”呢?在楚简《老子》甲本、乙本中,大多数“无”字都写成“亡”。根据《说文解字》:“亡,逃也。从入从乚。”“乚,匿也。象曲隐蔽形。”段玉裁注云:“亡,会意,谓入于曲隐蔽之处也”。所谓“入于曲隐蔽之处”指的是,本来在眼前的东西或者在手头上的东西遁入看不见摸不到的隐蔽之处。这也就是说,那些东西尽管都不在原处,但还都安然无恙地存在于别处。然而人们熟知的“无”并非属于此类情况。即,“无”的最典型的状况———例如木材的燃烧、鱼肉的腐烂等这些情况属于一些事物的完全的消失。即便是那些暂时离开身边而暂时遁入隐蔽之处的东西终有一天也都将化为乌有。这也就是说,人们所经验到的大多数“无”,是很难用“亡”字来表达得了的。正因为如此,后来“无”字的写法“亡”逐渐被“無”字所取代。 “無()”字在甲骨文中为“舞”的本字,“象人两手执物而舞之形。”[5]630而《周礼•春官宗伯》在叙述司巫的职能时指出:“若国大旱,帅巫而舞雩。”在这里,“舞雩”是女巫求雨之舞,是夏商周时代最典型的一种舞蹈。从本源上看,古代的舞蹈根源于巫女取悦神灵的动作,即女巫以跳舞的方式祈求神灵之保佑①。也正因为如此,“巫”字在甲骨文是从“無”字简化来的。因而“無”、“巫”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同一个字。不仅如此,“無”字同时还指巫女所要取悦的神。换句话说,“無”字具有三层意思:一指作为动作的舞蹈,二指作为舞蹈者的巫女,三指巫女所面对的神灵。[6] 不过,当人们用该字来指神灵的时候,这个“無”便指神的超越感觉的状态。而当古人不再把神理解为具有人格的超越者,而把它理解为不可预测的阴阳变化之状态时[1],指称神的“无”字的含义开始演变成为指称一个没有确定表象的状态,此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状之状”(《老子》第十四章)。 如此说来,“有”与“无”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就这两个文字最初所象形的对象而言,“有”指的是手上之肉,而“无”则指的是人所祭拜的神;就这两个文字的形上意义而言,“有”指事物的确定性表象以及质的稳定性,而“无”则是指不确定的表象以及质的流变状态。 自古以来,人们非常关注天地万物的稳定的秩序和确定的表象,因为这些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 但与此同时,古人还感受到这些可靠的东西之背后存在着一种无法把握的混沌的世界,而来自这个世界的变幻莫测的东西同样左右着人们的命运。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有”与“无”的关系呢? “有”“无”之“道” #p#分页标题#e# 《老子》第四十一章说:“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意思是说,天下万物都是“有”和“无”结合的产物,都是这两者相互转化的动态统一体。一方面,在不确定的混沌的“无”中不断地生成具有确定表象的“有”,此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而另一方面,从具有确定表象的“有”不断地转化为混沌的“无”,此所谓“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老子》第十四章)从这个角度看,天地万物莫不居于“无”与“有”的转化过程:或者处在从“无”到“有”的生成阶段,或者停留在从“有”到“无”的消亡阶段。在老子的时间意识当中,确定的、有序的表象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相反,该表象的世界的背面就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和无序的世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确定的、有序的因素与不确定的、无序的因素结合的产物,都是“有”和“无”的精妙的统一体。 “有”与“无”的这种关系还表现为“有名”与“无名”的关系。《老子》第一章有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名,可名,非常名。”一般说来,凡是天地万物都有其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质的统一性,因而是可以把握和命名的。但万物的这种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质的统一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这种把握和命名也不是永恒的。李白曾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写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的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本质都属于流变过程当中的暂时的停泊,因而这些“名”也只能是“非常名”。根据《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中国古人那里,天地是万物生成和留存的场所或者家园。 在老子看来,天地这一万物的家园发端于不可命名的混沌,而其中万物诞生则意味着可命名的状况的出现。如是说来,无名与有名在本源上具有相互关联性。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只关注这个世界的可命名的一面,而忽略这些背后的不可命名的一面。 问题是这后一点恰恰关涉到人的选择性和自由性。德里达曾基于原始部落的那比克瓦拉人的语言现象①[7]161谈到武断的命名所具有的原始暴力本性。他说:“它(命名)在差别中进行铭记,它进行分门别类,它将绝对呼格悬置起来。把这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放在系统中加以思考,把它铭记在那里,这就是原始文字的存在方式:原始暴力,专名的丧失,绝对贴近的丧失,自我呈现的丧失。”[7]162-163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使用语言来把握和命名事物,并以此来揭示各种事物最显著的特征,但恰恰是这种命名很有可能遮蔽各种事物不可命名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总之,“道”、“有”、“无”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词汇,而这三个词汇不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概念,其文字具有的特定表象内容具有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所谓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形而上者”是指,以这种文字的特定表象(“形”)为中介揭示出的普遍的象征意义(“上”)。 在《老子》文本中,“道”指人在十字路口需要选择一个出路的自由状态,“有”指犹如拿到手里的肉一样的那种被把握的事物,而“无”指犹如神一样无确定表象的存在状态。在老子看来,有与无、有名与无名之间存在一种循环关系:即,一方面无名、无序的混沌之流不断生成有名、有形、有序的万物体系,而另一方面这些有名、有形、有序的事物又不断地回归到混沌之流。这便是“玄之又玄”的宇宙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