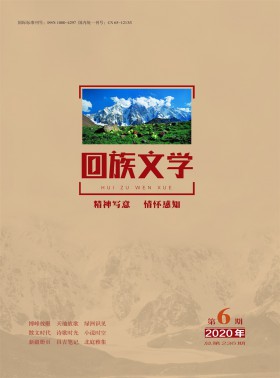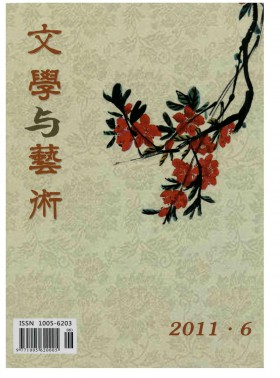一、写作的零度与意识形态观 巴特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否定首先来自于对“写作的零度”状态真实性的肯定。所谓“零度的写作”不能掺杂任何意识形态效应。为了撇清意识形态写作的混乱干扰,巴特采用了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在西方哲学中长盛不衰的经典范畴——“形式”与“内容”。在文学中,“形式”是指“文学性话语”的“构成机制”,“内容”是价值和意义与时代文化和社会背景演变之间的参照。“形式”关乎于能指,而“内容”则关乎于所指。在巴特看来,“形式”与“内容”相分裂后以“形式”也就是“能指”为中心的写作是现代性的写作方式,而“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写作才是纯正的原汁原味的古典的写作方式。古典语言是以字词及其关系为主导线索的,也就是说,字词不能离开与其他字词的关系而独立存在,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尚且还不具备独立的能指功能。单个字词的形式不会沉入一种内在现实,尽管这种内在现实是与该字词的外形现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而是在单个字词的形式刚一发出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词,从而形成一个“表层的意图链”。这种字词与字词之间的相互发散与延伸就构成了字词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得意义成为可理解的事物。但是在现代诗歌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现代诗歌完全是以“形式”为居中性的。单个字词的形式是具有豪门性质的“家宅”,单个字词形式就是一个具有独立存活能力的个体,并具有突然启示某种真理的能力。正如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写作比较一样,前者是古典写作的典型,而后者是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写作能手——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写作方式。“资产阶级的写作”首先是工具性的,其次是修饰性的。“福楼拜……根据一种劳动价值观的出现,明确地使文学成为对象,使形式成为一种‘制作’的项目……(应当说,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现为景象,被强加于读者)”。[1]5 现作使得作为内容的所指被作为形式的能指所统摄,目的是将一种观念强行施加于读者的目光,思想在这种虚无的欢快中上升,超越了整个逐渐凝固的状态。文学作为对象,首先是作为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作为劳动的对象,最后是作为被“谋杀”的对象。所以现代性的写作不再是作者自主性的创造活动,而是能指的宣告为王的加冕过程:能指-所指-景象-读者,这个链条表明了正是这种外界的制约性与主体选择的自由性之间的张力使得主体的自由选择成为无根据之物。因而出于保护合理选择的目的,人们应该摆脱掉各自意识形态的偏见,使真实的话语得以呈现。这样,巴特把摆脱意识形态偏见当作一种伦理性的选择标准。他认为写作就应该是无色的、不偏不倚的、零度的,任何作者的所谓道德观念都是被外界因素所干扰过的,写作需要摆脱社会价值判断,这样才能维持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性。 罗兰•巴特从虚构切入,发掘虚构中的真实状况,同时考察小说和历史所共同具有的文本的结构和功能,把结构和功能作为一种文学话语的形式分析问题,其实就是有关话语的真实性问题。“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模式在一种间接方法上得以表现,使得话语的真实性在历史和小说中获得聚焦点。他比利科更在意的是意识形态如何通过一种似真理的话语结构而得以形塑。巴特将对文本的怀疑主义的运作从文学分析转移到价值虚无的分析上来,他的这样一种论点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符号-价值载体”研究和鲍德里亚符号社会化批判提供了思想启发:作为“欢娱”或“欢快”原则的能指不过是一种虚无的“能指”,是没有目的的目的,是没有灵魂的灵魂。这样的表面快乐原则实质上是内心颓废的深刻写照,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物欲世界的真实镜像。巴特将文学写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首次清晰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在文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结合途中,符号扮演了某种中介或载体的角色,在卡西尔奠基符号学后,巴特将符号学发扬光大,为符号-空间批判(列斐伏尔)和符号-时间批判(鲍德里亚)提供前瞻性线索。 而“风格”是零度的写作的另一张面孔。或者这样表述会更加明确一些:零度的写作必须排除历史的干扰,并且它具有个性与共性的双重方面。零度的个性方面是风格,它是语言与其躯体内对应物之间的绝对自由的联系,是垂直性的必然式作用;语言结构是零度的共性方面,它是作者行为的场所,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反射,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与期待,是具有历时性的积淀,是水平性的否定式作用。风格与作家的性情相关,而语言结构则相反。它们看似对立,但都为零度的写作服务。在语言结构中,作者发现了历史积淀的熟悉性,而在风格中,作者发现了本人积淀的熟悉性。它们为零度的写作的服务体现在:“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因为他并不偏选任何一方”,“其中耗费的能量只表现在运用程序方面”[1]10。虽然风格与语言结构可以被例举和被转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识别和被选择。而一旦涉及到后两项,写作就必然会具有相应的温度。 在巴特看来,“风格”是孤独的,它不是艺术,风格不能成为把作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契约。历史对写作立场的困扰体现于一些喜欢艺术的安全性甚于风格的孤独性的作家身上。而能够在历史中拯救“新颖性”的也正是风格,它是一种权威,是作者语言和其躯体内对应物间的“绝对自由”。风格既在历史传统之中,也在历史传统之外。写作把作者带入了历史的境遇之中。而写作的零度状态并不是普遍性的,只有言语才可能是普遍性的。巴特在索绪尔将言语和语言二分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变革。索绪尔认为所有的语言学都是符号学的:“我们保留‘符号’这个词来指称这个整体,把‘概念’和‘音响形象’分别用‘所指’和‘能指’代替”[2]149,而此观点明显是被巴特继承的,但是巴特却对索绪尔的“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2]177观点进行了反拨。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符号现象,巴特承认了语言的社会性的内在特征,但是他认为符号学本就隶属于广义的语言学系统,因为倘若没有各种形式的语言,符号也无法借以表述和传播自己。所以,符号学领域不能被随意扩大到语言学中,否则就会引起严重问题:“把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符号学领域加以扩大运用并非没有引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显然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语言学模式不再适用而应加以改变了。”[3]18而巴特将其“写作”置于零度的设问中心,这样就不能避免言语与写作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它们的关系的研究,从而更好的让人们认清写作的真实面目。#p#分页标题#e# 而零度的这两张面孔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性的现实空间——作为实践的写作。语言结构与风格虽然是一种天性,一种先于一切与语言有关的设问,但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形式同一性”,却只能由外在于语法的规范和风格来加以恒定的确立。在“形式同一性”之中,写作的连续流被聚集和封闭于纯粹的语言学范围之内,进而转变为一套完整的记号,一种有关行动的选择。介于写作中保存着某种对“善”的肯定,写作成为伦理,成为作家介入幸福或不幸的表现与交往的体现。所以写作使得言语具有了既规范又特殊的形式,并和他者的广泛历史相联系,获得“社会化”的“交往实践”特征。而这种历史性的交往也必然带来了“异化”的困扰,这不得不使写作的零度冰封在历史的尘埃中。“语言结构与风格都是盲目的力量,写作则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语言结构与风格都是对象,写作则是一种功能”[1]11,在我看来,巴特所表达的意思是,“语言结构”与“风格”作为零度写作的两张面孔,并不涉及伦理,无论是哪一张面孔都不涉及美丑善恶;而写作的实践行为则相反。零度不是形塑的行为与实践,写作才是。由于写作实践的特殊性,使得形塑不得不存在于创造性与社会性的相互纠结的关系之中,并且被特定的重大的社会性目标所转换。由于写作“是束缚于人的意图中的形式,从而也是与历史的重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形式。”[1]11因而,写作是具有“价值”的“形式”,作家在写作中的相同的运动就是对其形式的社会性惯用法和对其所承担的选择的责任思考。这样,写作的本质就成了形式的伦理和社会性的场景选择。而这个社会性场景也绝不是一个实际的消费场,在此场景中,作家的写作选择是一个意识的选择(包括有意识与无意识),而不仅仅是功效的选择。 二、写作的温度与意识形态观 由于在写作层面的作家与历史现实发生了联系,这样就提出了零度的写作的必要性问题。巴特在写作中也区分了生产的写作与消费的写作两个层面。 作家不可能对消费的客观材料做任何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在言语的消费处,而是应当在言语的源头处,也就是言语的生产处,来要求一种自由的语言。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表述,那么写作的后过程——消费过程——流通过程,是作家无能为力的失效之所;只有在写作的当下过程——生产过程——形塑过程,作家才能使写作与一种历史的“契合”发生效应。这种“契合”所关乎的便是“能指的伦理”或“形式的伦理”,所关乎的是对“善”的判断与选择,这样就从源头处使概念与符号的无限衍义成为不可能。于是写作就这样成为一个含糊的现实:一方面作家与社会接触;另一方面,通过悲剧式的逆转,使社会的目的性返回到他创作的工具性根源上来。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历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种被自由消费的语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种被自由生产的语言。”[1]12 写作的伦理选择与责任便是“自由”,使得写作成为一种自由和具有对先前惯用法和新意指作用环境的“记忆的妥协物”。这种具有记忆作用的自由,是只能发生在其选择过程中,而不能发生在其传播-社会化的符号延异过程中。所以,写作的两个层面分别就是社会化的前后过程,分别发生在写作的实践-符号的形塑及其传播过程中。后者只能使人们沦为语言的囚徒,否则就必须具有法兰西学者的批判精神,这样,“简单的延续性逐渐使处于中止状态的全部过去和越来越浓密的全部密码显现出来。”[1]13 写作于是与“自由”一样,成为一种历史的“契机”,它的“密码”就是来自于作家的“意指性姿态”的意指作用。正如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之间的差异一般,他们的写作彼此对立显示了一种本质性的分裂的姿态,正好发生于两种经济结构相互连接的历史“契机”之时,两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之间。巴特内心深处的纯正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就此显现,这也是他继承他的偶像——马克思的地方。 这里可以展开的一个话题是:写作的零度何以可能?在我看来,零度的写作显然和物理学中的理想的零度状态是一样的,那只能是一个理想状态的乌托邦。只要人一旦被出生于这个世界中,就“被抛”入世,就不可能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不得不与周围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人只有在社会化过程中才能完成自我的成长历程。因此,写作的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否则只会带来生存的零度,社会化的零度,成长的零度。既然巴特为写作零度做的辩护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写作的零度既然是不能实现的,那么写作的温度又是几何呢?我认为,我们也不能以精确或瞄准式的刻度来衡量写作的温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获得相关的方法。 正如利科的文本“四重异化”观念一般,符号或文本的形塑、播散、解读过程都会发生异化,这样总是不停歇地向青年马克思靠近。而若从时间角度来分析,异化是发生在运动的过程中的绝对方面,而共时空下的符号结构分析就是一种保持相对静止的状态下的分析。写作不能以零度面目出现,但可以被人们研究它的温度。它有多少度是有意识地为意识形态辩护,有多少度是作者的无意识的偏见,还有多少度专门为自己的读者所设计?在我看来,除了异化之外,巴特自己所指出的“语言结构”最后充当了否定零度的角色,如果写作真的可以成为零度写作,在“语言结构”方面,无数个作者都会被固定于同一个文本的模型中。 当然,零度写作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特在零度写作下对“能指的伦理”进行拷问,人们也许还在无知觉地继续着虚无的欢愉,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零度写作来衡量写作的温度。 三、写作的符号与意识形态观 #p#分页标题#e# 巴特对符号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为了对符号拜物教进行批判,并反对概念的无限衍义。符号的解码与符号的形塑过程都使得意识形态或权力意志作为一种隐性的意指力量凝固在符号的权谋之中。 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区分在语言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区分。但是巴特认为,这并不代表了一种全面性的分析。语言结构和言语仅仅是对形象和行为的对象系统作这类区分,只是纯粹内化的分析模式。换句话话说,这不是在交互主体和交往实践以及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的全面诊断和分析,语言学需要上升到语义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巴特的符号学包括了社会化的符号意指系统在内。而利科的思想则更为全面一些:现实社会-意念-作者-社会化-交往实践-意指-符号-意指-交往实践-社会化-读者-意念-现实社会,就像是一个来回流动的拉链结构,把以符号为中心的理论流映照出来。 其中,巴特最关注的“意指”概念其实是从索绪尔的“蕴涵”概念繁衍而来,巴特对“蕴涵”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的结构形塑进行了研究,从而改造成为符号的意指功能,它也是巴特在梅洛-庞蒂的基础上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的“值项系统”进行改造后所植入的东西。因为索绪尔的“值项系统”仅仅导致了对有关语言制度的内在分析的承认的必要性;但内在分析的环节却与社会化-交往实践的研究相抵触,所以巴特认为反而是在哲学的视阈中,而不是在语言学视阈中,才使得系统获得了较为成功的发展。巴特认为,梅洛-庞蒂重新坚持了正在进行的-说着的言语(在产生状态中的有意义的意向)和已经被说过的言语(由语言结构所获得的结果,也是索绪尔的“蕴藏”概念所表述的意思)。梅洛-庞蒂对“蕴藏”概念的基础进行了扩大化,认为所有的过程都是以系统为前提和假定,发展出“事件”与“结构”之间关系的经典对立说,使得“蕴涵”也在历史学中取得了相应的公认的成效。 “蕴藏”概念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内也得到了重大发展。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言语”与“语言结构”的对立是“过程”与“系统”的对立,例如亲族结构内的女人的交流过程是这个对立关系的具体体现。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这种对立在认识论上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语言结构是机械的、或非“统计学”的、结构的解释;言语的研究则是统计学的、概率计算的、宏观的语言学;而后将言语吸收在语言结构之内,正是在这个吸收过程中,发生了无意识行为。巴特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一观点和拉康的无意识的意指理论相似。拉康的无意识的“意指”理论是欲望的表达,列维•斯特劳斯与拉康一样,把结构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列维•斯特劳斯最后归结为结构人类学理论。对拉康而言,索绪尔的失误正在于他无视了“潜意识”的力量和作者的论述“风格”。巴特借此也“意指”了自己的思想,“无意识”理论是可以被形塑于固定的结构中的。或许还可以导致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描绘“集体想象界”。集体的想象界显然也揭发了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在巴特看来,现在的人们都是根据“主题”来描绘这种想象,但是被拉康的无意识理论而转变这种想象,人们将根据形式和功能也就是能指来描绘这种“集体的想象界”,而后的遮蔽、意指、隐喻,也都与其欲望相关。巴特指出了索绪尔的失误之处。对索绪尔而言,记号是被论证为某种深层状态的纵向延伸的,在语言结构中,这种纵向化如果忽视了横向化,必然会使得所指位于能指之后,能指是所指的必要途径。事实真的如此吗?这种纵向化的思维方式是内向化的,不能实现社会化的表述,从而使得这种隐喻仅仅只能在空间化中发挥作用,失去了“意指的辩证法”。 四、结论 究其根本,巴特在文学中批判意识形态,从历史、实践、符号形塑的角度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统治性、幻想性和控制性,分析了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即便巴特后期从结构主义转向了后结构主义,他依然认为意识形态是寄生于符号的。利科从文本解码与文本形塑的双向研究中揭示权力话语的隐蔽性,而巴特早期更注重于符号与意指的形塑模型构架。巴特的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体现了法国黄金一代的璀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