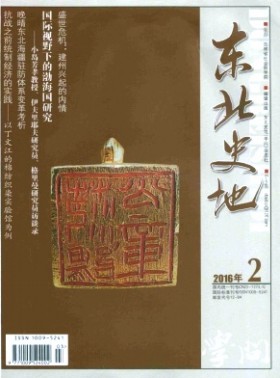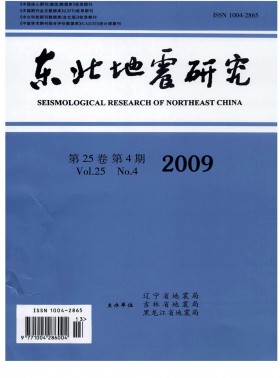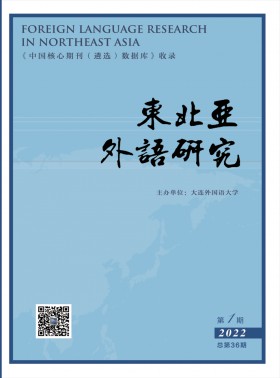考古学上反映的距今 3000 年前后,辽西地区自然生态和由此影响的经济形态的变迁, 在中国东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动因可以从气候、环境变迁和民族迁徙等多方面探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上自然生态的每一次大的变迁, 都深深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文明进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这无疑是今后东北史研究中应予以特殊关注的生态资源变迁问题之一。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其五, 具有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地域文化形态。以本文所举的“草原文化”为例。在这一东北西部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区, 几千年来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从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室韦、蒙古,尽管草原民族谱系的演变时有更替,但“草原文化传统”,却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续下来, 构成了东北亚地区连接中亚独立的地域文化区。
总括上述所举的五个主要文化要素, 即构成本文所说中国东北 “三大地域文化”———“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条件和稳定的文化要素。 当然在这种大地域文化下分别存在的“子文化系统”, 无疑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近来临江市依托鸭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成立了“鸭绿江文化研究会”,我认为就是“长白山文化” 大区域文化范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机构。 这些小区域文化的研究, 不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丰富资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纳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补充。
#p#分页标题#e#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是东北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始,以“汉———肃慎、挹娄———夫余、高句丽———东胡、鲜卑”四系的东北古代民族谱系一延续至今。④当前需要加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对宏观的东北民族史分布体系, 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二是对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民族谱系的审慎研究; 三是对研究薄弱的民族应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笔者 2004 年在《东北史地》第 5 期发表的《先秦时期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提出传统的西部“东胡—鲜卑”系民族之前,从当代考古学和先秦文献,“肃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记载看,在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应有一支更早于“东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学上的覆盖面广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东北民族分布辽西地区的早期民族谱系, 似应调整为 “燕亳———东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续了一千年以上,是上辽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国文明”。当然类似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种提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后者,对一些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统的东北“秽貊民族史”、“槖离、夫余民族史”和“鲜卑(三燕)民族史”等。 这显然与已有一个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极不相称。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以往如孙进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数注重地方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比证问题。 此次文章中, 孙先生在第十节“关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从东北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如此。诸如东北史研究中的区域文化与考古学类型的对应或演化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区系变迁的关系。 还有如何看待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与宏观的区域考古学分区的关系,如何审视处于东北亚腹心地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应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标志意义等。对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一文中,⑤曾经探讨性提出,在东北地区目前可认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应各有纵横二条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标意义。 其一为纵向的南北分列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其二为横向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 两者在东北考古学文化研究分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医巫闾山为辽西古文化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古文化(高台山文化和辽东大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汉辽西郡和辽东郡“汉郡文化”的明显分界线。后者张广才岭则是“长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东,包括“莺歌岭文化”和三江平原的“凤林文化”,与岭西松花江流域的“槖离沟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与李健才先生,为考察东北古代交通,曾对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迹进行调查, 即后来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第一辑中确认的“夫余(西团山文化)东与挹娄结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⑥。即张广才岭,在“长白山北系”的“北秽”域“肃慎”系考古文化分区中,具有分区标志意义。对上述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虽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凤林古城”代表的汉魏文化,多以“挹娄”文化属之,笔者倾向为《魏书》等记载“豆莫娄”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仅举上述“二纵二横”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区标识,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断得以俾证。
其二,横向的辽吉两省考古文化分区,我认为则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哈达岭)为代表。前者千山山脉横亘在辽河入海口和鸭绿江入海口之间,是辽东半岛沿海文化与辽东半岛腹地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的以“石盖墓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分界线,亦即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区。后者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属长白余脉的松辽分水岭。其明显地划分了辽东青铜文化与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南北两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同属东北“秽貊系统”的“南貊”与“北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线。即辽东的“貊系”文化,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文化,应以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界。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趋同:以医巫闾山和龙岗山脉等代表的山系,在东北地区, 其南北考古学文化上显现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别, 越来越得到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东北史研究与各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东北史与各专门史的关系, 实际上体现的是作为整个中国史组成部分的东北区域史与东北地区各社会专门史的纵横关系。 即中国东北史的体系, 总的必需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为基础。而各个专门史都应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横向展示各个门类、系统的专门发展史。诸如:东北生态发展变迁史,东北地域文化史,东北各民族专史,东北建置、疆域、交通发展史,东北人文领域的文化艺术史等。 其中还没有包括已从历史学科独立出去的新的一级学科东北区域考古学。 这其中从整个东北史体系来考虑, 过去除了东北民族史相对发展比较活跃外, 许多专史至今研究单薄或尚属缺环。如至今尚无系统的东北生态文明史、地域文化史、部族方国史和完整的民族、疆域、交通史等。至于总结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编著一部系统的东北区域考古学,也在人们的期待中。这里尚不包括具细的东北区系各民族史(如秽貊、槖离、夫余、鲜卑)和各东北断代史等。对整个中国东北史和各专门史研究存在的瓶颈问题, 首先是在确认东北史研究宏观分期、文化体系、基本民族分布体系和主要考古学类型分区的基础上, 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分类文化学上,总结梳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此基础上,协调组织具有研究基础的团队,进行不图眼前功利、不带“时限指标”的系统深入研究,其中团队的专家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如此,方能以期获得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成果, 否则只能停止在议论中。#p#分页标题#e#
总之, 本文只是从个人多年东北历史考古个案研究的体会角度提出的粗浅认识, 其中重点列出的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具有全局影响的五个重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恕请方家指正。
本文作者:王绵厚 单位:辽宁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