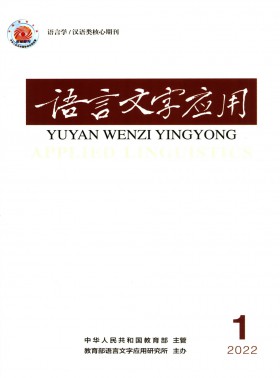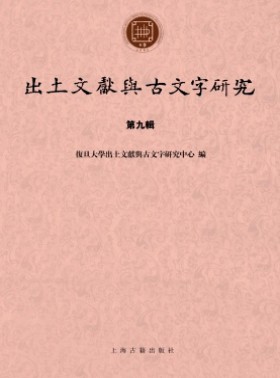我们认为,未被盗扰的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族徽文字,能够准确地反映当时的族氏关系,而被盗扰的墓葬因部分或大部分铜器被盗,通过族徽文字判断当时的族氏关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甚至完全失真。因此,为了使有关讨论能够建立在较为科学和客观的基础上,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的讨论,我们所选择的墓葬都是未经盗扰者,凡被盗扰的墓葬一般不予以讨论。但是,一个墓葬只要出土两种以上的族徽文字,无论其被盗与否,均不影响我们对该墓葬具有较复杂族氏关系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在讨论第二种情况时,我们对于铜器墓葬是否被盗扰,一般不作严格区分。
在商代考古发掘中,一个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情况时有所见。其年代较早者,首推2001年春季在河南安阳发掘的花园庄54号墓。该墓属中型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保存完好,未经盗扰,时代为殷墟二期,共出青铜器310余件,其中礼乐器43件,兵器170余件[1]。根据发掘报告已公布的材料,其中分裆圆鼎(M54.166)、圆鼎(M54.240)、甗(M54.154)、方斝(M54.43)、觚(M54.120)、钺(M54.86、M54.89)、卷头刀(M54.87)、矛(M54.113、M54.37)等器物上均铸有铭文“亞長”二字,在A型爵和B型爵等一小部分铜器上,只有铭文“長”字。据此可知,“長”为“亞長”的省称,应为墓主的族徽。按该墓出土有7件铜钺,又有大型卷头刀以及大量铜戈、矛等兵器发现,其中Ⅰ式铜钺呈长斧形,长40.5、刃宽29.8厘米,重5.95千克,仅次于妇好墓所出的大铜钺,说明墓主是当时的一位高级军事首领。发掘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族名“長”前冠以“亞”称相符,说明“亞”为商代武职官名“,長”为族名。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从以上情况看,花园庄54号墓属于只出一种族徽的墓葬,可知一个族氏使用一种族徽的习俗,至少在殷墟二期就已经形成。我们知道,一个族氏名的出现,它决不是孤立的,一般与其他族氏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会在族氏的标识即在族徽文字上有所反映。那么,花园庄54号墓所见的長族,是否也与其他族氏存在着某种联系呢?1997年~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发掘的长子口墓,为我们认识長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长子口墓位于鹿邑县太清宫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初,它是一座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大约晚于花园庄54号墓300年左右。该墓出土青铜器235件,计有礼乐器85件、兵器46件、工具14件、车马器78件、杂器12件[2]。其中有铭铜器54件,均为礼器:铭一字者4件,铭文为“子”;铭二字者3件,铭文为“子口”“、戈丁”、“尹舟”;铭三字者39件,有37件铭文为“長子口”,另2件为“□父辛”;铭四字者2件,铭文均为“長口子口”,亦即“長子口”;铭七字者3件,铭文均为“長子口作旅宗”;另有3件字迹模糊,推测可能为7字,其中2件可辨识的铭文为“父……”,1件为“子口□作……”。从以上铜器铭文看,有42件铭刻“長子口”,加上显系对“長子口”不同称谓的“子”、“子口”等6件,共计48件铜器可以确定为长子口器。一般认为,“長”是族名,“子”是身份,“口”为墓主私名。如果把长子口墓与花园庄54号墓进行对比,显然长子口墓出土的4件3种族徽为花园庄54号墓所未见:1件是族徽为“尹舟”的铜觯(M1.143),1件是铭文为“戈丁”的铜斝(M1.196),另2件是族徽为“”的方鼎(M1.46)。、戈、尹舟都是商周金文中的常见族徽,三者同时在长子口墓中出现,说明当时的長族与这三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是联姻、联盟,还是同族或隶属关系暂且不论,仅这三种族徽在长子口墓中出现,本身就足以说明商末周初的長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要比殷墟二期長族与同时代其他族氏关系更复杂。这种情况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花园庄54号墓规模比长子口墓小,因而族氏关系较长子口墓简单;二是长子口墓的时代比花园庄54号墓晚,因而族氏关系显得比花园庄54号墓更复杂。这就是说,对于同一族氏来说,族组织规模越大,则其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在不同时代,同一族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时代越后,则族氏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
在商代中型墓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族徽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要比小型墓葬更复杂,这类例证不胜枚举。例如,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共出土青铜器123件,其中有铭铜器24件:三字铭者3件,铭文为“亞”;二字铭者16件,铭文为“亞”;一字铭者5件,铭文为“亞”[3]。从盖、器同铭的情况看,方彝盖铭为“亞”,器铭为“亞”;方罍器铭为“亞”,盖铭为“亞”。由此可知,“亞”、“亞”、“亞”都是同一族氏。发掘者认为“,亞”是墓主人的称谓,“亞”是其职官名,代表其身份与地位,“”为其族名“,”可能是支族名或私名。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按照这一认识,我们可以将该墓有铭铜器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铭“亞”者5件包括铭“亞”者16件,共计21件;另一组是铭“亞”者3件。显然,从铜器的数量上看,铭“亞”者是铭“亞”铜器的5倍多。这种情况说明,前者与墓主血缘关系远较后者更为亲密,二者与墓主有较明显的亲疏差异。因此,将亞和亞看成是同一族之下的两个分支,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刘家庄北1046号墓族徽所反映出来的同族分化现象较为典型,它说明一个族氏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会不断地分化出新族氏,而新族氏的族徽一般是在旧族徽上附加新称号,以示其与旧族的渊源及区别。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些墓葬中,族徽文字反映出的族氏关系不能简单地用族氏分化去解释。例如河南安阳郭家庄26号墓和160号墓,均为保存完好、出土器物丰富的中型墓葬。前者时代为殷墟二期,出土铜器61件,其中有铭铜器8件,6件铭“旅止”,1件铭“”,1件铭“□宁”[4]。这种情况说明,墓主应当是旅止族,该族与、□宁二族可能因联姻、联盟或其他关系,曾得到过这两个族氏赠送的助葬之器。郭家庄160号墓葬规格较高,共出土青铜器291件,其中有铭铜器41件,铭文四种:其一为“亞址”,计有33件;其二为“亞址”,计有3件;其三为“亞止”,计有5件;其四为“中”,计有3件。其中“止”为“址”之省体,可知“亞止”同“亞址”,而“中”又与“亞止”分别铸于同一器上,说明其族与“亞止”关系密切。这样看来,郭家庄160号墓的所出族徽,实际上主要有“亞址”、“亞址”两种。从铭文看,“亞址”与“亞址”中都有亞、址二字,说明他们拥有共同的族号,可知二者为同族关系。从铜器数量看,铭“亞址”的铜器远远多于铭“亞址”者,又说明“亞址”与墓主的血缘关系远比“亞址”更为亲近。按照子为父祖送葬的常理推断,可以肯定“亞址”与“亞址”是兄弟之族,他们是同一族的分化。在该墓出土的一套3件铜铙上,铭文“亞止”又与族徽“中”同见于一器。这种情况说明,“中”有可能是与“亞止”有联姻或联盟关系的族氏名称。总之,从郭家庄160号墓所反映的族氏关系来看,它至少包括两级族氏结构:其一为“亞址”与“亞址”,他们是兄弟之族;其二为“亞止”与“中”,他们可能是联姻或联盟关系。显然,这两种关系是构成该族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
与前述中型墓葬不同,商周考古发掘的小型墓葬,一般一墓只出一种族徽,这种情况较为多见。我们知道,一个家族铸造铜器数量的多少,与该族的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有关。商周考古发掘所见小型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现象,应当是这些家族经济能力较弱、规模较小、结构较简单的反映。1986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南共清理了29座商代墓葬,其中M29、M25属于殷墟二期墓葬,未经盗扰,保存完整。前者出土有2件有铭铜爵(M29.1、M29.5),铭文均为“寢印”;后者也出土有2件有铭铜爵,铭文亦为“寢印”[5]。按两墓同处一地而铭文相同的情况判断,说明这是同一族氏的两座不同墓葬。1983年在河南安阳市薛家庄东南发掘的商墓M3,是同时发掘的6座墓葬中未被盗扰的一座,出土有鼎1、觚1、爵1、戈13、铃3,共19件铜器。其中爵、觚所铭族徽为“象”,铜鼎所铸族徽为“象”[6]。“象”与“象”见于同一墓葬,应为同一族的两个不同分支。这是小型墓葬中较少见的一墓出两种族徽的情况,说明较小家族的结构虽然简单,但自身也存在着分化。郭家庄商墓M38的时代为殷墟二期,保存完整,未见盗扰迹象,但在出土的铜器中,只有1件铜戈上铸有“山”族徽[7]。按该墓出土铜器甚少的情况推断,“山”应当是一个较小家族的族号。1991年在安阳后冈发掘的38座殷墓中,有一座编号为M33保存完好的殷墟三期墓葬,在出土的铜觚上铸有铭文“”,铜爵铭文为“辛”[8]。“辛”为墓主的日名,“”为墓主的族徽。1963年春在苗圃北地发掘的M172共出土铜器9件,其中鼎、簋、卣、觚、爵上均铸有“亞盥”族徽[9],时代亦为殷墟三期,这也是一墓只出一种族徽较为典型的例子,但在同类墓葬中所出铜器较多,说明其族经济能力较强。在殷墟四期小型墓葬中,一墓出一种族徽者如安阳郭家庄商墓M50出土的鼎、爵上,均铭有族徽“兄”[7];刘家庄商代墓葬M9出土的鼎、爵、觯上,均铭有族徽“”[10];殷墟西区第八墓区商墓M1572出土的爵、觚上,均铸有族徽“”[9];安阳刘家庄商代墓葬M2出土的爵、觚上,均铭有族徽“宁”[10];殷墟西区孝民屯商代墓M2065出土的铜鼎上,铭有族徽“京”[9]。综观以上墓葬,其共同点是规模较小,出土铜器数量不多。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当时这些族氏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地位不高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原因,似乎主要与这些族氏在各自宗族结构中所处地位有关。可以这样认为,由于这些族氏是构成各自宗族的基层组织,族氏结构单一,故多见一种族徽。相比较而言,在一些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族徽,而这些族徽所显示的族氏结构和族氏关系则较为复杂。例如在前述中型墓葬中,郭家庄商墓M160出土的“亞址”和“亞址”族徽所显示的是同一族氏的分化;而鹿邑长子口墓出、戈、尹舟等族徽所显示的是不同族氏的结合。这种情况表明,族氏关系的复杂性通常在规模较大墓葬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然,规模较小的族氏也存在着族氏分化,如前述薛家庄M3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在商周考古中,一个墓葬出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的现象较为常见。这类墓葬目前发现时代较早者,首推殷墟妇好墓。妇好墓位于小屯北地,墓室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器物极为丰富,是公认的殷王室墓葬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该墓出土铜器468件,其中礼器210件,有铭者190件,加上有铭兵器和乐器6件,共计196件。在这196件有铭铜器中,根据铭文可以直接判定为妇好铜器者111件,约占全部有铭铜器的57﹪,其余为司母辛5件、司母26件、亞弜6件、亞其21件、亞啟3件、束泉22件、聀1件、文1件[11],共计85件,占全部有铭铜器的43%。这种情况说明,妇好墓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较复杂。从甲骨文有关记载来看,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可知该墓所出铜器上的“妇好”或“好”是私名而不是族徽。妇好墓所出族徽文字主要有亞弜、亞其、亞啟、束泉、聀、文6种。关于这6种族徽各自的情况,必须充分估计如下两点事实:一是妇好为女性,其死后随葬器物中,按常理必有其娘家所在族氏所赠送的陪嫁器物或助葬之器;二是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其死后的随葬器物中可能含有被征服的方国或族氏之贡品。关于前一种情况,我们目前尚无法指出哪一种族徽可能是妇好娘家的族名。关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依据该墓出土的玉石刻辞可稍作推测。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上,有如下两条刻辞:其一为“卢方入戈五”,见于玉戈(M5.580);其二为“妊冉入石”,见于石磬(M5.316)[11]。“入”有贡纳之义,是武丁时期常见的记事刻辞,辞例一般为“某入”。这说明妇好墓随葬器物中确有其他族氏或方国的贡品。有学者认为,亚弜组铜器有可能是妇好生前所得的贡品,因为亚弜鼎的形制较早,出土时的情况表明其为妇好生前用器,而且“弜”作为族名见于甲骨记载,其地望在豫西,与殷王室关系密切[12]。我们认为,在殷墟甲骨文记载中,多见弜族参与征伐,亦参与祭祀,如“弜”(合集23178),说明弜与商王室很可能是同族关系,而且亞弜圆鼎规格较高,通高72.2厘米、重50.5公斤[11],故亞弜铜器不可能是贡品。但是,妇好墓中的器物来源较复杂,其中既有亲属助葬赠送,也有贡纳或掠夺所得。这是应该承认的,它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墓葬出有几种族徽的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与妇好墓类似且互有关联的殷墟二期墓葬有小屯M18。该墓位于妇好墓东南约22米处,共出土青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者共13器:铭一字者5器,4件铭“戒”,1件铭“正”;铭二字者4器,1件铭“正侯”,1件铭“鳥”,2件铭“子渔”;铭三字者4器,铭文均为“子母”[13]。在这些铭文中,其中“子渔”见于武丁宾组卜辞,其所参与的祭祀对象都是商王室的直系祖先,说明其身份为王室贵族。据董作宾先生考证,子渔为武丁的嫡长子[14]。从小屯M18的时代看,它打破了殷墟文化一期的房基,所出陶器介于殷墟二、三期之间,墓室规格、形制、随葬物等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一般,正与殷墟卜辞中武丁嫡长子“子渔”的身份相称。从该墓的空间位置来看,它与妇好墓相邻,妇好为武丁的配偶,子渔是武丁的嫡长子,儿子死后葬于母亲墓旁,亦属合乎情理。在古文献记载中,武丁有一个儿子为祖己或称孝己,相传孝己的母亲早死,武丁因惑于后妻之言杀害了孝己。这些传说正好与卜辞曾占“子渔有疾”有联系,而与妇好墓旁发现M18墓葬的情况相合,故学者多认为是文献记载中的孝己就是小屯M18铜器铭文和卜辞记载中的子渔。上述这些方面,是确定小屯M18墓主的主要证据,也是我们认识该墓所出族徽及其复杂族氏关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子渔”是人名而不是族徽。这样看来,小屯M18所出族徽实际上只有4种,即“正”、“戒”、“子”、“鳥”。其中“正”又见于侯家庄西北冈M1001、M1004,这两座墓葬是公认的王陵,时代属于殷墟二期。这种情况说明,族徽“正”可能是出自殷王室的族氏。按传世器中有一件形制为殷墟二期的铜壶,铭文为“帚好正”(集成09509)。“帚好”即妇好“,正”应为妇好娘家的氏名。依此推测,子渔墓出土的族徽“正”有可能是子渔舅氏的族名。“戒”与“鳥”,我们目前还无法推知其与墓主子渔的关系。至于“子”,从甲骨文有关“子族”、“多子”等记载,可知它是指子族。王国维指出,金文“某母”乃女子之“字”,为女子的美称,古女子无论已嫁未嫁皆称母[15]。由此可知“子母”之“”应为私名。如果这一认识不误,说明子渔墓中有同族女子所送的助葬之器。
同一墓葬出土几种族徽的现象,不仅在殷墟大、中型墓葬中存在,而且见于小型墓。这类墓葬数量较多,下面按铜器分期略举数例说明。在殷墟二期小型墓中出土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文字者,主要有小屯M17。该墓共出土随葬品10件,其中陶器7件,铜器有鼎、觚、爵各1件,铭文分别为“”、“”、“”[13]。从这三者关系看,我们无法判断主次。但是,这座墓葬位于小屯村北,与妇好墓接近,时代也相同,说明它属于王室贵族墓葬,而族徽“”又见于侯家庄西北冈王陵M1550,其它两种则未见。由此可以推断,M17墓主的族徽应该为“”,是属于王族之下的一个族氏。1980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东南发掘的M539规模较大,共出土有青铜礼器14件,其中有铭文者5件:一字铭者1件,铭文为“”;二字铭者3件,铭文分别为“亞”、“鼓”、“出”;三字铭1件,铭文为“辰出”[16]。这些铭文,按族属可分为两组:一组为“”、“亞”,其族名为“”;另一组为“出”、“辰出”、“鼓”,族徽为“”。显然,这两组铭文对应的是两个不同族氏。从铜器数量上判断,墓主的族名应为“”。在“”组铭文中,“出”“、辰出”“、鼓”应为同一族氏的不同分支。诸如此类的殷墟三期墓葬,还有河南安阳戚家庄东269号商墓。该墓出土有铭铜器17件(不包括资料未发表的有铭铜戈10件),其中族徽为“爰”者14件,族徽为“子”、“”、“疋未”者各1件。一般来说,这类族徽主次明显,数量较多者应为墓主族徽,其余族徽均可视为与墓主有姻亲或其他关系的族氏名号。因此,戚家庄东269号墓墓主的族徽为“爰”,而“子”、“”、“疋未”是与爰族有联姻或联盟关系的族氏。在有些墓葬中,一墓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还反映着墓主生前所在族氏的结构。例如1982年发掘的小屯西地M1共出土青铜器礼器19件,其中有铭铜器6件,除1件族徽为“重”外,其余族徽均与“庚豕”有关,单铭“庚豕”者3件,族徽为“庚豕马”者2件[9]。从各器亲属称谓均为“父乙”的情况看,可知“庚豕”、“庚豕马”必为同一族氏的两个分支。但有些墓葬所出土的族徽,并不容易看清族徽所代表族氏之间的关系,即使到了铭文较多的西周时期,也是如此。例如1967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的西周墓M1,该墓出土的23件礼器中共有11种不同类型的铜器,其中12件有铭铜器上有10种不同族徽(、、、劦册、、、、、徙遽、虎),而且亲属名有“父丁”“、父癸”“、父辛”、“父乙”、父己”“、母辛”等[17],各不相同。现将各器族徽与亲属名连缀情况列举如下:爵(M1.18):“父丁。”角(M1.19):“劦册父丁。”觯(M1.21)“:父癸。”斝(M1.20)“:父辛。”卣(M1.12):“父乙。”盉(M1.17):“乍父己,徙遽。”尊(M1.15)“:子夌乍母辛尊彝,。”从以上各器的受祭者看,大部分为“父某”,只有最后一件为“母某”,表明受祭者以男性祖先为主,也有女性祖先。
从族徽来看,可知他们属于不同族氏。这就说明,以上铜器不是同族人所做,原本是献祭给各自祖先的,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又同时在白草坡墓M1中出现,说明墓主生前与这些族氏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白草坡墓M1的墓主为“潶伯”,这有3件铭文为“潶白乍寶尊彝”的铜器(M1.13、M1.14、M1.16)为证。如果这一看法不误,我们便可得出结论说,这些不同族氏的铜器,可能是与潶伯有姻亲或联盟关系的族氏所赠送的助葬之器,也可能是潶伯生前通过交换、贡纳或其他方式所得他族之器而被埋入墓中的。1971年陕西泾阳高家堡村西周早期墓葬出土有铭铜器5件,其中尊和Ⅰ式卣上的族徽为“”,盉、觯及Ⅱ式卣上的族徽为“戈”,亲属称谓则有父己、父戊两种[18]。从铜器数量上判断,该墓主族徽应为“戈”,而“”应是与戈族有联姻或联盟关系的族氏。曹玮先生曾对西周各铜器墓葬进行过较为细致的分类分析,他依据铭文能否辨别墓主,将西周铜器墓葬分为三类:一类是依据铜器铭文不能辨别墓主人的墓葬,一类是可以辨别墓主人但随葬有其他人铜器的墓葬,另一类是只有墓主人自己铜器随葬的墓葬。他认为,第一类墓葬的随葬铜器不是属于一个人的,其铜器来源有多方面,有一部分应是墓主生前曾经使用过而死后随葬在墓中的,一个墓中出现多人祭祀各自祖考的铜器,说明这些铜器不是为墓主一人而作,而是当时家族之间的赗赠;第二类墓葬主要出现在昭王至夷王时期,它是人们开始仅仅祭祀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祖考,而将放入墓中的铜器逐渐变为只放墓主本人祭祀先祖器物的一种发展;第三类墓葬是西周后期礼制严格化以后,限制非墓主铜器的随葬,礼器赗赠也受到限制的表现[19]。曹先生的研究角度与我们不同,重点在于探讨西周时期的赗赠制度,但其对西周墓葬铜器的分析,基本上与我们前述从商代墓葬考察中得到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西周赗赠制度可以上推至商代,其实质是各族氏之间存在的联姻或联盟关系的反映。
综上所述,从殷墟二期以来的商周青铜器墓葬来看,同一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现象,是同一族氏分化及沿袭关系的反映;而同一墓葬出土几种族徽的现象,则是不同族氏之间存在联姻或联盟关系的反映。正确认识族徽文字所反映的族氏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商周社会家族结构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商周青铜器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现象,笼统地视为同一族氏血缘关系之反映;而对于同一墓葬出土几种族徽的现象,又多以嫁妆、贡物、赠品或战利品解之;未曾深入商周社会家族结构。我们知道,一个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他必然要与其他人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对于一个族氏来说,也是如此。因此,一个墓葬中出土几种族徽的现象,应是族氏之间存在联姻、联盟等多种联系的反映,而不是对族徽标识族氏作用的否定。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族徽并没有起到区别不同族氏的作用,不能解释族徽使用与分布跨越族属的现象,说明大多数商代和西周早中期的“图形文字”应为祭礼的标志,而不是所谓的族徽[20]。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这种看法的实质是把族徽所反映的族氏关系作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从根本上否定了族徽文字的性质,其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族徽文字所反映的族氏关系非常复杂,它需要对有关的考古材料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本文作者:雒有仓 单位: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