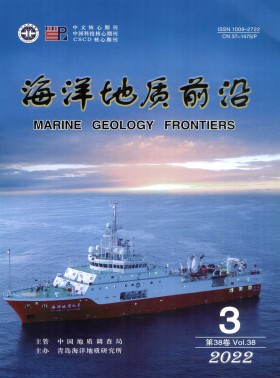作者:黄鹏 单位:中央戏剧学院
话剧表演中的舞台艺术语言应该鲜活生动,具有“动态性”。动态性的艺术语言,要求演员以自身的呼吸和发声器官为主要创作工具,利用“重音”、“语调”、“停顿”等技巧,有变化、形象地反映和表现人物精神世界、内在感受,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创造。这种有节律和具有艺术美感的语言,并不是一般声音的塑造、语句的堆砌,而是一种具有形象性的艺术语言。演员对角色形象的理解和构思,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动态性的语言得以体现,从而帮助演员创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一)动态性的舞台语言必然包含着复杂的人物内心感受
舞台语言的“动态性”,就是语言表现力要“灵动”。在创作中语言想要“动起来”,创作者势必要紧紧抓住规定情境,势必要有强烈的内心依托。演员对规定情境进行分析和感受,挖掘人物此时此刻的心理脉络,通过有对比性的语言,充分抒发内心情感,形成“峰峦相连”、“此消彼长”的语言感觉,生动地传达人物激烈的内心活动。这样一来纵使话语不多,依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佶在《蔡文姬》的排演中,谈到了他创造曹丕这一角色时,专门提到了一场戏:曹操要让董祀自裁,而曹丕希望通过自己的提醒,让父亲回心转意。
曹丕是乖巧的,颇识体统,但不狡黠。出于对父亲、文姬和董祀的爱护,他当然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要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用比较妥帖的方法来提醒父亲。他先让周近下场,观察一下父亲,然后轻轻走在父亲身旁,说出了这句关键的台词:“父亲,文姬夫人何时召见?”态度上,既有对丞相的恭敬之礼,又有君臣之间的商榷之规,也包含着父子之间的私情,语气上,既轻又缓,特别强调了“文姬夫人”几个字,意思是“您是不是再听听蔡文姬的另面之辞?”短短的十几个字,表明了曹丕积极参与这一矛盾的决心,而参与得又是这样得体。父亲听后,稍候片刻,说:“我再做考虑。”我想,“噢,他采纳了我的提醒,但他是否马上就能行动呢?这是我所担心的。”曹丕带着这种心情,接着说了三个“是”字。三个字有间隔,第一个“是”比较兴奋,第二个“是”比较担心,第三个“是”甚至有些沮丧。随着三个“是”字,后退了三步。刚一转身,父亲叫了一声“子桓”,我很快把身转回来,又升起了希望,当然,这也许是一个使我失望的回答,但这也有可能是个有希望的兆头,我很快回应“在!”“关于文姬夫人的情形……”为了能清楚地表达急切等待的心情,我把脸转向观众,眼睛闪闪发光。曹操接着说:“……你可以好好查询一下。”啊!父亲毕竟是纳谏的明君,事情是有挽回余地的。他的话音刚一落地,我兴奋地说:“我一定留意!一定留意!”……(《蔡文姬的舞台艺术》-69页,苏民等编著)在这场戏中,董行佶的语言并不多,但是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利用寥寥的几句话,就将曹丕这个人物跃然于台上。这不能不说是在台词处理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文姬夫人何时召见?”,将“文姬夫人”点出,恰恰就是在婉转地提醒曹操,同时又在表明自己的态度,确实做到了“突出重音”。这种重音的突出并不是煞有介事地重读,而是在不动声色之间,显现了自己的态度,这恰恰就揭示了曹丕这个角色的行事方式,人物性格———谨慎、不乏智慧。后面的三个“是”字,则是充分运用了语言的对比,富有动态。就像董行佶所表述的那样,在这三个“是”之间,包含着角色大量的思想活动以及此时此刻对现场的感受。三个“是”字,中间有两个语言上的停顿,完全是揭示了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活动,对待事物的态度。同时,也就曹丕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只有曹丕才是如此,换作别人未必会这样周密细致。通过这番语言,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于台上。
(二)动态性舞台语言在创造过程中必然结合着艺术构思和设计
话剧表演艺术需要演员的感性,但也少不了对角色的理性构思和设计。这些构思和设计,要从最大限度上调动和梳理演员的感性创造能力,使其服务于创作。一块好钢如果没有外力的挤压、锻造、塑型,那么永远只是一块钢而已,无法实现价值最大化。演员对待角色,在富有创作热情、情感饱满的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技术、设计,把这如同钢水一般的热情、创作天性和能力,注入到角色的身体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完成和深化角色的创造。在中央戏剧学院台词课中《荒原与人》的独白、对白教学阶段,我深刻体会到了构思和设计的重要性。创作中的构思不是凭空想象,必然要结合脚踏实地的理性分析。这种工作其一,是剧本准备过程中的案头工作,包括分析人物的前史、人物所处的规定情境、人物的思想线、情感线、心理线,人物此时的行动、人物的贯穿行动……其二,是以上分析的深化,在之前基础上,能够调动自身肌体的一切创作可能性将分析的东西展现出来,并且在展现的过程中寻找灵感迸发的瞬间。这种展现是演员在创作中一系列理性分析和感性分析的物化,在舞台艺术语言创作中,会对语言的形成起推动的作用。不论是在演员自身的形体上、声音上,还是在演员与舞台景物的相互关系上,都必然会反过来对演员的创作造成影响,从而在语言上有所改变,使演员能更快地融入规定情境中,找到属于角色的心理形体自我感觉。从这个角度讲,动态性的舞台艺术语言既是艺术构思和设计的目的,也是深化角色创造的必然要求。
在《荒原与人》“送细草”一场戏中,一对男女学生用“红绸”这一物件对戏进行诠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运用“红绸”编排了一系列的舞蹈动作,在舞蹈中完成了对白。“送亲”中,红绸是显而易见的物件之一,这场戏运用红绸在逻辑上完全行得通,顺理成章;而用红绸来体现细草和马兆兴这一组人物关系,更是巧妙。两个演员在舞台上运用形体语言,充分调动了自身的情感,将两个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彼此的爱恨情仇生动地演绎出来。细草上场时,一条红绸横据台中,似乎揭示了她的命运———去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她要面对命运中的强大阻碍;随着马兆兴的上场,这条红绸又将两人远远隔开,隐隐如同一条激流,使两人相望却不能牵手;随着故事的进程,这条红绸又化为缰绳,既系在命运的马车上,又是两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牵绊。两个学生说出的语言相较于以往在张力上明显有所增强。所有的语言不仅是在行动的过程中说出的,而且伴随着更加积极主动的形体动作,以舞蹈推动语言,以语言诠释身体的语汇……整个表演处于“动态”之中,使舞台艺术语言的表现力得到大大增强。#p#分页标题#e#
(三)“动”中寻“静”使舞台语言具有鲜明层次
任何戏都不可能一个节奏到底。即使是在矛盾冲突最尖锐的时刻,人物的内心斗争达到顶峰,人物的外在表现也不见得就会等同于这种内心节奏。在很多时候,这种内外的反差会使人物更加真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所谓“欲左先右”,“欲扬先抑”,在变化中寻求鲜活的生命力。同理,舞台语言也是如此。在上述的“送细草”一段中,虽然情感激荡,但两个角色有好多独白并不是喊出来的。
演员说台词要有感受。首先,在表演中十分的感受未必就要用十分力说出来,可能用三分力效果能更好一些,举重若轻,点到为止。再一层,独白是自语,人之所以有自语,必然是因为有感受到的东西,也必然想要把它抒发出来。有谁会自己冲自己吼叫?至少在生活中我没见过。在舞台上,可能会因为艺术的夸张性会出现此类情况,但是这不是单纯的嘶吼,而要包含着深切的心理体验。
请看这两段独白:马兆新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从一开始细草就不是我的,现在又终归还给了别人。我马兆新不过是一段插曲……两年前的夏天,是我马兆新开着拖拉机把她和垦荒队的伙计们拉到落马湖;两年后的冬天,又是我马兆新赶着爬犁把她送出垦荒队,送进从底窑迎来的吹吹打打的娶亲行列……一个小伙子亲自把自己热恋过的女人送到别人家去当老婆!不,不是热恋过,我至今还在爱着她,要不然我不会这么痛苦。那么,为什么不拦一拦她呢?她是失过身,她身上有个孩子,一个别的混蛋男人的孩子,可那怨她吗?她当时象我一样,我们都还年轻……可马兆新是个男人!男人!(更加凶狠地抽打着辕马)细草男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可是,女孩子就不是人吗?哦,不去怪他吧!如果在他回来那天,我去向他倾诉他走后的一切,他会谅解的。小马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可是,我不但没讲,反而要嫁出去,这对小马就象是火上加油。我为什么这么干呢?也许,我也有自私的一面?我想用这种举动进一步激起小马的爱?我这样想过吗?没有吧?可是,他为什么不拦我一下呢?只要你马兆新说一句:“细草,你是我的!你不能走!”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可是,你没说,你这是在报复我!男孩子的心真就这样硬吗?(《荒原与人》,李龙云著)马兆新和细草两人,在此时已是心力交瘁。他们的内心苦楚,因为彼此的隔膜无法用言语沟通,所以只会越来越苦,使他们感到窒息。经过了一系列的打击,早已经是身心疲惫。说话时,我想,更多的是无奈、彷徨、疲惫、疑惑,而不是在发泄。那么,在语言上,演员尽量采用舒缓的方式,相对安静地,感觉着,叹息着说出台词,会不会更好一些?在整个片段处于积极行动的情况下,注入这么一点“静”的因素,反而会使创作中的舞台语言整体感觉上更加棱角分明,层次清晰,富于表现力,使这种语言上的“动态”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