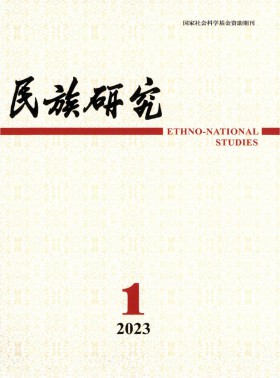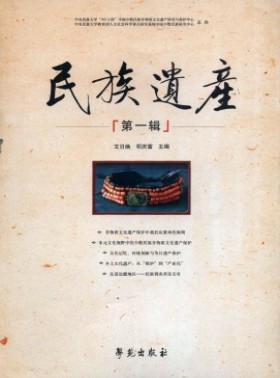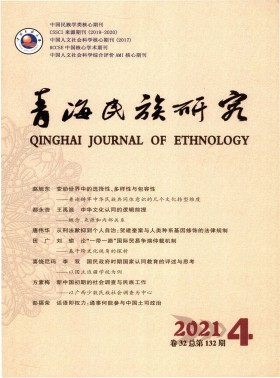作者:罗晓飞 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羌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生活在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民居作为一种建筑形式经历了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至今,在吸收多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仍然保持其独特的风格特色和浓厚的古风遗韵。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就描述了今岷江上游的古羌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室”的情形。在秦穆公独霸西戎使生活在青海河湟地区、渭水上游草原地带的古羌人四处迁移,不再是“西戎牧羊人”的民族而开始定居下来事农兼牧后,以修房造屋为主的建筑艺术便应运而生。其“用乱石垒成的辉煌”如今依然如梦一般展现在世人面前……和群山相融,与天地相接,似一幅幅壮丽、古朴的画卷让人魂牵梦萦,留恋往返。
建筑是造型艺术,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和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它是时代的写照,是艺术、文化、科技高度集中的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反映了文化的时代、民族和地域特色。我国当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的。所以,它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强烈,也更重要。”羌族民居建筑是羌民族文化的象征,是该民族历史发展无言的史书,是羌族文化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最初的“安居”目的的造屋形式到如今的民居建筑艺术,期间,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让世人感慨万千。其民居建筑一般都是由上百户或十几户人家集聚而居,形成“羌寨”,选此修建多在依山傍水的河谷、半山腰和高半山地带。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变化、延续发展已自成体系,并形成独特的造型风格与审美内涵。是这个古老民族生存观、宗教思想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和精神体现,是羌民族形象的代表和文化的纪念碑。
一、羌族民居建筑的造型、结构、存在的空间与作用
羌族民居建筑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虽然今天的建筑面貌已远非其原始状态,但在其建筑选址、房屋布局以及空间形式等方面,依然保持了浓厚的古风遗韵,呈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反映出羌族民居建筑早在几千多年前就已形成的规模和风格特色,并为后来的羌族乃至藏族(嘉绒藏族)等民族的民居建筑打下了深刻烙印。
(一)、建筑选址:历史上,在羌人艰难的生存环境,辗转流离的命运中,大自然是他们精神的寄托,灵魂的依托,因此传统羌寨的选址忠实地反映了人们的信仰,对朝向的选择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在羌人的风水观中住宅和聚落选址一定要躲开山体的遮蔽,以便透过山间,遥望到远处连绵的雪山。因为远处巍峨的雪山是神的象征。“羌人特别崇敬山神,因为他们认为山神主管着山中的物产,羌区每年举行的祭山会(又称转山会)上,释比(相当于汉族的巫师,是羌民族精神领袖)要假托神的旨意宣布乡规民约,号召羌人严格遵守,通过原始宗教的形式调节羌区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羌区聚落的生态环境。”[1]羌民族至今仍然保持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
(二)、外部形态:羌族民居建筑为石片砌成的平顶房,呈方形,在造型上分内外结构。楼层布局大多分三层:底层为牲畜圈,二层住人,三层为晒台。在羌族民间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就有关于羌人住房的记载:“石砌楼房墙坚根基稳,三块白石供立房顶上,中间一层干净人居住,房屋下面专把禽畜养。”羌族建筑大多为三层楼的格局与羌族的宗教思想有关。因为羌人以为,居楼的结构就象一个人,中间是心脏,顶层就是一个人的头,楼顶上供奉的白石则是人们头顶上的天神化身。所以现在的羌族民居,我们常见在房顶和房四角堆放着白石,这也是羌人“白石崇拜”宗教观在民居建筑中的体现。建筑的房顶一半全敞开、一半全封闭,形成了灵动而富于哲理的造型结构,这种格局是符合羌人尊崇自然、吸纳灵气的宗教思维的。羌族民居建筑整体布局遵循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自然法则,依山而建,因势造屋。房屋与房屋之间摩肩接踵,高低错落;建筑技巧上大量运用“挖眼搭木”、“靠墙立柱”和“共用墙壁”,以此节省劳力和财力,同时营造出宏伟的城堡气势。
(三)、内部空间:“在羌人的意识中,住宅从来都是是神人共居的空间。住宅的室内结构布局亦必然反映出人与神的各种复杂关系及沟通方式。劳作起居与宗教,神圣与凡俗在羌人的生活中没有界限的,永远和平地共居一室。”[1]羌族民居内部空间复杂而多变,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是羌族居室文化和宗教思想的集中体现。羌族是原始宗教烙印深刻的民族,至今仍保留“多神崇拜”的宗教观念。这种文化在居室中的火塘、神龛、中心柱上有明确的体现。1、火塘:火塘是羌人家庭生活的中心,是家庭中最神圣的区域,由于火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羌人形成了火神崇拜的传统。其造型由早期的三块白石(又称“三石顶一锅”)被现在的铁制三脚代替,底部凿成圆火塘。“火塘既是羌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又是羌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羌人与祖先、神灵间沟通的桥梁,受到了羌人的膜拜,并且还是体现羌族社会凝聚力的标志”[2]。2、神龛:神龛是羌民族精神寄托的重要所在。在传统的羌族民居中,神龛位于进主屋门的左前方屋角,用木板制成,有秩序地贴满了灶薇花(一个大鼎中插着莲花的图案),羌族人称之为“神衣”,是羌族每户必备的陈设。作用是供奉家神,包括天、地、国、亲、师诸神,还有观音、牛马二王、财神、门神、灶王、文武天子、羊神等,也有笼统称为“角角神”,体现出羌人希望通过供奉诸神,保佑家庭平安,六畜兴旺的朴素心理。3、中心柱:中心柱属于羌族民居中墙承重与梁柱承重结合的结构,由于天气寒冷及火塘位置的关系,主屋成为主要的活动中心。中心柱便在主屋的正中,地位崇高,禁忌很多。“中心柱还蕴含有超越功能的‘恋祖情结’,在羌族社会中还能起到了维护宗族和家庭内部团结、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与火塘、神龛一样,具有很强的精神慰籍功能。”[2]
(四)、碉楼建筑:碉楼在羌语中又称为“邛笼”。是羌族民居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是羌族民间建筑的标志性符号。在长期的实践中,以碉楼为中心,形成羌族独有的建筑布局。“早期碉楼的功能主要用于战备,各寨中碉楼的排列多成三角形布局,达到提前防御和隐蔽御敌的目的,还可将宝物藏于碉楼之中,有效地防备山匪、强盗的抢掠,在冷兵器时代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2]碉楼形式多种,有四角、六角、八角碉等,甚至有十二角的碉楼(茂县黑虎羌寨碉楼);造型上窄下宽,呈梯形状,全用片石砌成,高度二十至三十米不等;在功能上分哨碉、战备碉、风水祭祀碉等。用作祭祀的碉楼,有一定的神圣感,是族群的象征,与通天柱、生命树有相似之意,是羌人的一种“图腾”。碉楼还是全寨的最高点和中心点,是在寨内判断方位的指示标志。在结构布局上,有的碉楼单独修建,有的与住宅结合修建,浑然一体。#p#分页标题#e#
二、羌族民居建筑艺术的审美意味
建筑是有意味的形式。“建筑是以视觉要素为主来进行设计的空间造型的,其视觉要素的形、质、色按一定的形式美法则交互综合,可以构成千姿百态的建筑形态。”[3]建筑形态是由几何形体构成,但其形式表现力极强,有凝固的音乐之称。形式美感是建筑审美的决定要素。羌族民居建筑以其优美的外部形态,合理的内部空间分配,严谨的布局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羌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应该说是中国民族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体味羌族民居建筑其美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正如,“对建筑艺术的审美,是人类一项独有的、高级的、特殊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是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4]我们在感叹羌民族宏大、深沉的建筑艺术的同时,也为古羌民族曾经走过的沧桑赋予建筑艺术的“震撼”美,以及呈现的民族精神特质所折服。羌族民居建筑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一)、宏大、雄伟、壮丽之美
走进羌族地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山顶上或是险要关隘上高高耸立的碉楼。远远望去,一片黄褐色的石屋顺陡峭的山势依坡而上,或高或低,错落有致,其间碉楼林立,气势恢弘。走近一看,便可发现这些碉楼雄伟坚固、棱角突兀。碉楼作为羌民族独有的建筑,既是技术又是艺术,既具备一定历史时期的客观性又不失时代特征的观赏性。其造型挺拔、高耸,呈多边梯形向上空发展,在视觉效果上呈现独立、巨大特征,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突兀、雄奇、震撼的力量。同时,建筑本体的多面多角向上倾斜,它产生一种强大的向心向上的凝聚力,因为石片的垒砌是向上向内收缩凝聚的,无数个片石相互之间无间的契合保证了碉楼干百年来竖立的坚固,形成羌民族地区一道亮丽风景。羌族建筑文化的传统性和民族性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其建筑形制不仅是民族宗教信仰的表征,更是羌族民居建筑文化体法自然,与生态永恒的象征符号。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对建筑的讴歌:“如果人生纯属辛苦,人就会仰天而问:难道是我所求太多以此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和纯真与人心为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但还有诗意的安居于这块土地”。古羌人长期生活在天高地广的大草原,后又迁徙到高山险峻、江河急流的川西北岷江流域,这样的环境给人以雄伟壮丽审美精神的陶冶。所处的地域环境,又创造出自身的艺术感染力。
(二)、强烈、朴实、厚重之美
羌族民居建筑结群而居,由十几户至上百户形成规模宏大的羌寨建筑群体。因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之巅,其建筑群体又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街市”和“古羌王遗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特有“奇观”。羌族民居建筑因地域环境制约,其建筑材料多为泥石和少量用木,因时地宜,就地取材。在大自然赐予的“天然”材质的同时,也造就了古羌人精湛的建筑技艺。在山岭、在云端大面积的土堆石砌一方面是原始本色美的再现,另一方面其创造可谓是“神工意匠”、“背山起楼,巧夺天工”,其力量是震撼的、巨大的。“羌族的建筑原料是自然生态的,建筑的过程也是体法自然生态的过程。”[5]“羌族尊重自然石,树的本性”。其材质的特殊性和自然和谐相处生态观,赋予了羌寨建筑本身的“地域色调”和质朴、厚重的建筑材质美,也成就了羌族民居建筑如“雕塑”般的形式美感。“建筑的形式美一直是建筑师所追求的,当建筑师把地域的文化,历史等方面应用雕塑的形式美来表现,其建筑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4]羌人作为处于长期迁徙的民族又处在大山环境之中,以山地为伴,生存环境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民族性格是坚韧不屈、刚毅朴实。因而其建筑艺术在审美特点上表现出刚健朴实与厚重。同时,羌人祖先艰难困苦的迁徙经历成为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构成了内心世界深层的情感因子,并成为民族深沉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根源。
(三)、祖先崇拜、自然至上之美
羌族的宗教信仰还停留在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阶段,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羌族民居室内的中心柱就是典型的“恋祖情结”,其宗教功能超越了其建筑本身,赋予了居室建筑神秘、神圣的光环和浓郁的宗教色彩,是祖先崇拜在羌民族建筑艺术中的表征体现。羌民族从最初客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观化为人与神、物的关系,虽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在传延知识体系,规范行为模式,维持社会传统上,有重要作用。其民居建筑艺术审美不仅是视觉上的行为活动,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情感共鸣和陶冶。古羌人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以自然至上的生态观在建筑史上不失其作为建筑“时代性”特征。“羌族的石砌文化建筑以及其包含的宗教观念与精神价值的显现,是包含人类以自然的物质,自然的手段(与工业化相对而言),和谐自然的精神意识,宗教信仰来和合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建筑文化文本,具有很高价值”[5]羌民族民居建筑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文化,当我们想起任何一种重要的文明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用伟大的建筑来代表它。“人类文明开始以来,人们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通过无数次的生产劳动,有意无意地总结出一些共同经验,这些共同经验演变成为群体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人的内心深处沉淀成衡量美的原型标准,符合这种标准的建筑激发出读者隐藏的潜在心理本能,得到群体的共鸣,于是被公认为是真正美的建筑。”[4]我们在岷山中穿行,不时能够看到富有特色的羌族的碉楼和石砌房。羌族民居建筑正是以碉楼、石砌房等享有盛名。而古羌碉楼的建筑技术则是华夏文明一颗耀眼的明珠,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200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亨利博士在考查理县桃坪羌寨时,称羌族碉楼建筑为“世界建筑明珠”、“东方金字塔”。数千年以来,许多杰出的文化巨人都充分肯定建筑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羌民族的建筑物,就充分证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