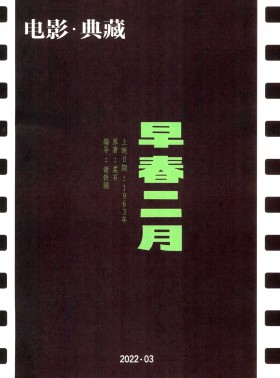1960年金基德出生在韩国庆尚北道奉化郡,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山村里长大,自小热爱绘画。父亲是一个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母亲是一名普通主妇。9岁那年全家移居汉城,金基德在一所农业技学就读。中学还没毕业就辍学走进工厂,从此在那里度过了青春。20岁时,金基德应征入伍。五年后退伍,在教堂寻得一份差事,同时坚持画画。1990年金基德前往法国,在巴黎深造美术,并靠卖画为生。两年后回国,贫困潦倒的他开始尝试剧本写作。1993年,他的剧本《画家与死囚》获得剧作教育协会最佳剧本奖。 1994年,《二次曝光》获韩国电影委员会最佳剧本奖,次年《非法穿越》再获该奖。这些奖项使他在1996年筹得资金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鳄鱼藏尸日记》,从此走上了职业电影人的生涯。 金基德电影的特点是以极端的性和暴力反映人性和民族的深刻悲剧,绝不回避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探讨,但大多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其影片中遍布着各种充满暗示的符号,比如鱼、岛、少女往往具有极强的形式感。女性在金基德电影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往往是剧情的关键,矛盾的核心。金基德电影虽然以韩国人为刻画对象,但大都直指人性深处,具有整个人类的共性。金基德虽被很多人非议暴力,但他在残酷冷静之下其实探讨的是人性的救赎和对人类处境的深深悲悯。 金基德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工作者,他的作品总是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和共性。无论影片的结构、叙事风格抑或画面审美,都仿佛被烙上了金式品牌般的显著和出类拔萃。 其实这多拜他坚持独立创作所赐,他多方面的才能使他每次都身兼编剧、导演和美术数职。而能始终做到这一点并很出色的导演在世界影坛屈指可数,大概也只有日本的冢本晋才能与之媲美。有趣的是这两人都很钟情于“压抑”的风格。综观金基德作品,宏观上可归为两类。一类如《收件人不明》、《野兽之都》等叙事性影片,大抵情节饱满、故事性颇强,多为边缘人的群体写照。缺点是往往剧中众人物的矛盾冲突过于集中化,会让观众感觉略显牵强。另一类相对叙事性较弱,却是在人物个体的性格和内心刻画上施加极浓笔墨,如《漂流欲室》、《坏男人》等。美中不足的是有点晦涩,娱乐性稍差。 在《春去又春来》之中,金基德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将东方佛学的“轮回”与西式基督的“赎罪”捆绑在了一起。 童僧用石头压住河中一条鱼的尾部,绑住一只青蛙和一条蛇。暗处,老僧无声地看着兴奋妄笑的童僧。在童僧睡觉时,老僧将一块沉重的石头系在他的背后。第二天起床,童僧背负着石头一一为那些被他物束缚的青蛙、蛇、鱼解脱。 当看到死亡发生时,童僧开始悲伤地痛哭。起初是一个施者,但后来成为一个受者。主人公这种“施者”、“受者”双重身份的获得,又被给予了对于另一个“受者”处境的发现,最终看到了自身的现状及未来的苦痛,便产生了金基德影片之中一个重要的情感命题———“同情”。在《春去春又来》之中,此种“同情”更多侧重:感同身受或同病相怜的感情,前人看到的永远是后来者犯下自己当初犯下的罪孽,而自己永远要为后来者赎罪,从根本上讲,也是为自己赎罪。这样一个往返不断、此消彼长的过程在构成一个又一个“轮回”的同时,又极大地契合西方所坚信的交替着原罪与赎罪的人生,而统一这两种不同哲学命题的方式又是相同、相通的情感。与此同时,“同情”也是“移情”,尽管两者并非完全等同,但在人类情感里,它们的发生往往总是相生相伴的。 在《萨玛利亚女孩》之中,一个援交女孩死去,对于“同情”体验的争取与对于“赎罪”行为的努力,直接促成另一个女孩用自己的身体重新去和那些与死者有过性行为的中年男人再次发生关系,再把金钱交还他们。但是,这一情节发生之前,同情却是以移情的形式获得暗示:每每卖身完毕,第二个女孩都会在澡堂为第一个女孩咒骂着清洗身体。对于援交这一行为,作为真正的行为者丝毫感受不到痛苦,相反非常快乐并主动为之,却总是由那个为她清洗身体的女孩承担着这种世俗所不允许的行为在精神上引起的苦痛与污浊。 创作的不同时期,“移情”与“同情”的各自比重与运用方式,构成了金基德对于世界、人生态度变化的重要参照。在最近的作品《呼吸》中,“移情”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情感含量,也占据着极大化意义。 童年曾溺水窒息,有过“濒死恐惧”的少妇,与划破自己的喉咙试图自杀的囚犯,通过分享一种因为呼吸器官被破坏而引起的接近死亡的共同感受而产生了感情。明天便要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早已成为一名被世界除名的人,对于这样一个被排除在正规环境之外的死囚,开始获得了同性恋、心理问题者等那些在世俗中无法获得解脱的人的同情。少妇与囚犯在监狱的会客室发生关系之后,捏住囚犯的喉咙,试图将其亲手杀死。此时,囚犯已成为了一个被移情的对象,承担着事不关己的他人的罪恶,以自己将要被处决的污浊的身体,给予他人一个重返人世的机会。最后,少妇走出监狱,丈夫与女儿在门外等待,三人在彼此雪球的袭击之中破涕而笑,化解困境。究竟是出自于“自身”还是“他者”,对于感情,尤其在死亡面前,情感往往极其难以界定。以“爱慕”为形态存在,而这种“爱慕”却又因涉及自身问题的投射成为了迫害,所有爱慕者将这个被世界除名的囚犯当做自身问题解决的途径,在社会刑法执行之前,先用自己的问题堆放在他的不被保护的身体上,将其杀死。至此,《呼吸》之中,同情的眼泪、爱意的眼神、激烈的交合都成为这种自私发生的掩饰性前提。 金基德众多的电影通常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闯入者”。金基德片中的“闯入者”既是《漂流欲室》、《春去春又来》后期出现的警察,又是《弓》里代表着文明社会的诱惑,带少女离开古船与老人的年轻大学生,以及《萨玛利亚女孩》跟踪女儿、殴打嫖客的父亲。在“闯入者”未出现的前期部分,这些故事都构成了一个又一个远离伦理文明社会,但又可以自成一体的荒诞和谐,比如提供淫乐的漂浮着的河上小屋,笔记本记录着的身体交换,古船与老夫少妻,然后,“闯入者”的出现往往会直接对这些“异物”行使所谓文明社会之中的正常的“法”与“惩罚”,从而将本来的自成一体带入一个混乱或毁灭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些身负世俗价值框架的“闯入者”在本质上总是刻意或无意地误读着主人公的行为与情感,他们是“同情”的不通者。然而,在《呼吸》之中,这种“闯入者”却以另一种形态与作为得以在场。#p#分页标题#e# 由金基德亲自扮演的永远坐在监视机前的监狱长,不但没有像以往一样一味地破坏与阻止不伦关系的发生,起初甚至正是这样一位“闯入者”才得以促成少妇与死囚见面。每当两人想要进一步发生身体关系时,监狱长都会按下按钮,结束他们的见面,从而行使了闯入者的权利。但最后,在监狱长的纵容下,两人还是完成了身体的交合,然而,这种与死亡过分贴近的爱欲与同情,最终导致少妇试图将自己遭遇过的濒死体验施加在了死囚的身上。 对于金基德以往的电影,杀死嫖客的父亲、驱逐妓女的警察、带走少女的大学生……这种种毁灭都是由“闯入者”完成的,而在《呼吸》中,不伦关系的毁灭却是令行为者本身去行使的。 道德外力的消逝、当事人的自我解决、关系的自行毁灭促成了金基德电影体系之中一种意义的变化,在《呼吸》之前,“同情”的被毁灭多数是用于谴责世俗的不理解与独断性,而“闯入者”便是这种外物侵入的集合形式。《呼吸》的处理却从对外在世俗的谴责走入到对内在人性本身信心的丧失,作为电影本身,在《呼吸》之中,尽管美术师出身的金基德越发地表现出了设置格式化及过度设计等问题,电影中的人物依旧在那些特定的、被明确固定过的、意味丰富的场景之中表演,但这种所占比重甚大的移情效果与闯入者行为的变化也令金基德的作品提升到了一个更加宿命、绝望、残酷,甚至放弃抵抗、不再试图解决、不再试图寻找症结所在的境地之中。但或许当“对抗面”从外部转向内部,真正认知路径、成长道路才开始渐渐地显现于我们的面前。 2006年拍摄的《时间》更把社会残忍与扭曲美混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带有浓重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批判的对象是堕落虚伪的国民性(韩国已经是一个假面的世界),这不由让人回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敕使河原宏和安部公房合作的《他人之颜》中的著名场景: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戴着面具的人们。一个对于本相不确信的民族是变态的,韩国人和杰克逊一个德性,无论是改变大饼脸的企图还是妄图把自己民族幻想成东方的代表都是他们虚伪的表现。在文本逐渐消失的年代,阴性的溪流将记忆涤荡干净,回忆成为篡改的方法,那生死相约的爱侣其实已经和往事无关。 《时间》从情的角度确实可以读解,可是,我认为,《时间》是金基德对于变态韩国的可怕预言书,在他的背后隐藏着暴力和偏执的情绪,这是崩溃和极端的信号,韩国是我们应该密切注意的近邻,它甚至比为军国主义者招魂的“靖国神社”更加可怕。 金基德的电影中的爱、孤独、寂寞、残忍、兽性和无奈组成了他电影中的“元音”,也是现实社会每个人心深处最不愿意被他人所窥探的部分,存在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对尘世的茫然,在静静的沉默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无奈的人才会沉默得如此彻底。每看一遍,那种对现代社会人与人的距离感、孤独感、失落感的认识就会加深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