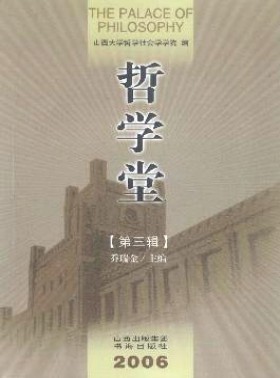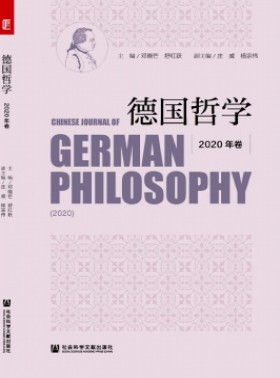作者:周海英 高华丽 单位: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维特根斯坦的“说”与“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多处谈到了不可说的东西“,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可说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他看来,能用语言或逻辑形式表达或分析的,是可说的,但逻辑形式本身正如摹画的形式,是无法言说的。以往哲学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于不能正确使用语言产生的。(杨寿堪,2011)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实证科学才能摹画世界,“善的本质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凡是自然科学命题,是可说的,自然科学命题之外是不可说的。(杨寿堪,2011)美学伦理学都不是实证科学,因此“不可说”。“真正说来,哲学的正确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事情。”(Wittgenstein,1992)“可说”的涵义,是指能够用一般的语言,即语言哲学中所述的命题,来进行描述。可说,就是能成像的。可说的进一步解释就是最终能显示或能得到映射的,可捉摸的,否则就是妄说,即“不可说”。“推而论之,不可说的即为虚的抑或隐的东西。”(董惠宁,2010)维特根斯坦的“说”与“不说”与中国传统哲学观中的一些理念不谋而合。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提出的“道”,即自然运行法则,是代表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是学理上或理论上不可变易的原则性的道。
二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翻译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论,意即诸如美学伦理学,是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的。从美学欣赏角度看语言文字,语言何尝不是一种艺术,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学?根据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并不是以全新的身份参与阅读的,读者原来累积的审美评价和审美体验会在其阅读活动中融入到现在的阅读中,姚斯将其称为“读者的前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这一系列的前理解在阅读中能被保存,并在新的阅读中被运用以及再次被识别,这种前理解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这种前理解是什么?又能否用言语刻画出来?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曾有艺术家提出,在毕加索、米罗的画展上,不少美术专业学生追问:“这些画好在哪里?”这说明他们还欠缺审美意识,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在审美价值的基础上,当面对新的审美对象时,原有的评价标准出现了偏误,无法对新的审美对象做出正确的评价。个人审美的体验及审美评价是非常微妙的,审美意识的建立也有赖于不停地对比、评价、批判、肯定等这样反复的过程。在建立了审美意识之后,从现有的审美意识出发,去评价作品形式的情感意味或剖析作品所激发审美体验的形式因素,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需要一定的“悟性”,这就是一种“不可说”的概念。
文学创作活动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方面交流的动态系统。作家创作的文本在未经读者阅读前只是“潜在的”艺术作品,它并非完满的自足体,有着许多“未定点”和“空白”,它的意义有待在读者的“接受屏幕”上实现“具体化”。接受美学最显著的观点就是突出了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一方面,它承认了作者的创造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读者对作品实现的积极参与,既承认作品的客观存在,又肯定读者的主观创造。在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文本中的这些“未定点”和“空白”并不是文本本身传递出来的,而是读者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意识创造出来的,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感受是不同的。法国作家法朗士曾说,书的实质只是印成的成串的记号,书所晕染的色彩和情感是靠读者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去添加的。正是这些绚烂的色彩,撼动了我们心灵的情感,才赋予了书中这些记号以生命,让它们都活跃起来,让书生气盎然。接受的过程是读者依赖自己的审美经验创造作品的过程,每个读者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体验,他们给作品带来的意蕴也就因人而异了。除了读者的自身制约因素,作品范围规定也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感受,从而使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
翻译的过程涵盖的又要远比欣赏文学作品复杂,当读者拿到一部作品时,心里就形成了一种阅读期待,即期待从作品中读到什么,获得怎样的审美体验。读者按前期阅读期待创设一个参照值,读者与作者的经验以这个参照值为基础,相互交流、融合。前期阅读期待受作品本身的题材影响,也受读者原来对类似题材作品的阅读感受制约。译者对原作在通过自身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体验解读之后,赋予了作品新的涵义,这个感知、加工、创造的过程是“不可说”的。经过译者的阅读,作品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作品,而是经过再加工、再创造之后的新的作品。译者跨越了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将信息重新编码,转换成新的语言,这个过程中,语言本身对译后文本产生了制约作用,因此,译后的文本已不是译者脑中的那个作品,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不可说”的。译后的文本到了目标语读者眼中,目标语读者又要根据自身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体验重新解读,并再次重新创作他们心中的新文本。如此反复,从原作到目标语读者心中重构的作品,这中间影响的因素很难用言语来叙述、刻画。
三翻译中的“意会”和“言传”
综上所述,文学创作即是将“不可说”的概念用“可说”的语言进行最大化的摹画,让读者能在心中重构一个世界,翻译也是如此。“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李洪儒,2007)20世纪,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促使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译者作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纽带,同时关联着两种语言。语言工具论者把语言当作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只不过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Saussure,2001)正如杜威所说,他将语言看作一种关系,语言是以拥有共同交流群体的两个不同个体之间互相作用的方式,这两个个体都属于这个群体,并从这个群体中获得了言语习惯,能为双方所理解,所以语言体现的是一种关系。同一种语言尚且如此,跨越两种语言的关系就是复合的关系网络。翻译活动中的译者,正是游走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一直以来,翻译理论研究者都在致力于研究翻译的实质,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早在周代,就有了从事翻译的官员,“寄”、“象”“、鞋”、“译”,虽然称谓有异,但指称的都是从事类似翻译性质工作的人员。通过这些名称的演变,我们可管窥中国翻译发展的历史,对翻译的基本定位是一个“传”字。“传”是将一种物件或言语传递到另一处的活动,它强调的是物件或言语的完好无损。就言语而言,“传”的最高境界是不改变原有的文字形式,即将语辞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对方。(肖平,2004)按照对翻译的最理想化的理解,应该是将语辞以及伴随语辞的逻辑形式一起原封不动地进行传递。而在现实操作中,译者就发现了其中的难度,也就出现了“意会”与“言传”两个概念。#p#分页标题#e#
语际之间之所以能相互转换,主要是基于语言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翻译理论研究者将其称为“信息转换通道”。但由于不同的语言有其特殊性,不同语言下的文化更有其独特性,当“信息转换通道”受阻时,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就产生了。洪堡特认为,所有的译者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原作与本族语言永远都是译者的绊脚石,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这两块绊脚石绊倒。如果译者贴近原作,就会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反之,如果译者靠近了本民族特点,就会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于找到,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洪堡特,1796)。洪堡特所提到的并不只是说译者在夹缝中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表达方式确实存在着差异,他还提出,“即使出自完全不同的语系的语言,即使它们从未直接或间接地相互接触,并且属于不同的类,它们的结构也必定具有某些普遍的相似。”这些普遍的相似,即“理性的智力本能”的表征,与老子的“道”、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是一个道理。
“不可说”在翻译中的理解主要基于两方面:第一层就是存在于所有语言体系后的这种普遍相似,让两种不同的语言能进行相互转化,某一事实的表达在不同语系里用了不同的编码形式,但却能找到其在不同语言中的对应。这种普遍性存在于语言之上,无法用语言来进行表述。第二层的“不可说”存在于语言之间,英国翻译家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根据产生不可译的原因,把不可译分成了“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这两个不可译性都是存在于语言之间的。“语言结构通常体现出某一语言文字的结构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般只能在同系语言或同族语言之间找到对应体……而类似转换却很难在非亲属语言之间实现,因为非亲属语言之间语符需要完全换码。”(刘宓庆,1993)不同语言体系下的语音、字形和语言效果实现手段都有差异,这些都是只能在该语言体系下意会的,而无法通过翻译来获得同等的效果。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也表现在文化的不可译性上。每个国家、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使得在翻译中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寻找到相应的语言符号来对应这些“文化负载词”,译文中也就失去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
对于翻译的“不可译性”,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译者的“可说”与“不可说”主要是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表达方式的斗争。语言的表达能力对应的是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是各种语言的共性;语言的表达方式对应的是实现语言表达能力的方法途径,每种语言都有其差异性、民族性。共性与个性对立存在,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这种说法固然有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我们对求同存异的包容心。“可说”与“不可说”作为矛盾的对立面,二者相辅相成。翻译中如果都追求“大同”,语言、文化也就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意义;只有存在着“不可说”,才有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千姿百态的文化形态。这些“不可说”的东西,是要通过心灵及情感去感知的,而非用言语直接刻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