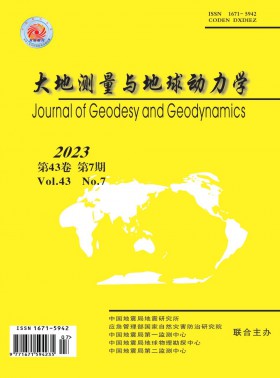作为当代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力求确立一种有别于西方启蒙精神所倡导的新伦理观念即生态伦理观,从而使人——社会——自然三者面对当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能够保持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而以何种理论为建构的逻辑基点,是这一伦理观缘何能够得以确证的关键之一。其中强调摒弃以人为惟一价值主体的传统伦理观念,视一切自然存在为道德关怀对象的生态伦理学整体主义,特别是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恰恰能为此提供理论基石。其原因就在于,生态伦理观的确证开启了人类伦理观念的新维度,其本质是对传统的本体视阈的一次尝试性拓展。对于生态伦理学而言,“本体”的样态不再仅限于以往自然式的、思辨式的以及社会式的,而是一种以生态学为依托的生态化的本体。本文将从大地伦理学的生态学范式和生态共同体理论入手,力图达到对生态伦理观的解读。 一、大地伦理学的生态学范式:生态伦理观之根 如何从规范的角度对当今生态危机作出解答,并确立恰当的生态伦理观念是生态伦理学不可规避的问题之一。为此,生态伦理学整体主义的倡导者——利奥波德借助生态学作理论范式,通过拓展人类伦理关怀对象的阈值,也就是从具有理性主体地位的人延伸到整个生态系统,进而为伦理观念的生态化提供理论前提和伦理预设。那么,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的生态学何以能够有助于生态伦理学实现如此的规范性拓展呢?这就在于生态学内隐的有别于其它具体实证科学的强烈的形而上的整体意蕴。生态科学就是以其自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世界观图式,也就是复杂的、生态的整体性世界观;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态的行为模式。而这两方面协同作用的结果,就使生态伦理观的建构获得了恰当的逻辑基础。因为任何一门科学不仅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工具,而且也为我们提供如何进行实践的基本知识。 就生态学自身的理论特点而言,它通过研究生物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强调以整体的观念看待自然,并逐渐形成了循环观念、多样性观念和平衡观念。当代生态学使我们确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人类只是自然的普通一员,是生活于自然世界之中,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比如,新生态学的奠基人埃尔顿把群落模型理解为一个能量模型,并用隐喻性的生物共同体描述出一个由食物链和食物网构成的一个能量循环的金字塔。这一思想对利奥波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从早期的保护主义走向生态主义。在大地伦理学中,利奥波德把大地金字塔结构(生物区域金字塔)视为一个由土壤、植物、各级动物构成的能量群落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土地不仅仅是土壤,它是能量流过一个由土壤、植物、以及动物所组成的环路的源泉。食物链是一个使能量向上层运动的活的通道”。[1](P205)本质上,就是通过描述生物区域内的各级食物链、食物网络以及其中能量流动,使我们得以从生态的、整体的视角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所有物种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的动态性和过程性的实体意义,从而为自然的道德身份提供了基础性原则。大自然的动态过程性表征着其自身内在的一种生存状态,它让我们在体验自然的动态进化过程中感悟到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是以人为判据,而是源于自然创造生命的过程,由此获得对生命的敬畏之情,这种情感就是一种对自然的伦理关怀。这样使我们赋予非人的其它自然物以道德关怀的地位就变得可以理解。 所以说,对于道德身份拓展问题的解答,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是基于生态学提供的相关知识,采用生态学范式确立生态共同体概念,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完成了对生态伦理观的构建。 二、大地伦理学的生态共同体:生态伦理观之本 共同体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那一时期共同体范畴的内涵是很宽泛的,例如,家庭就是一个给人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指出共同体具有多样性,城邦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共同体,并且作为整体的城邦在本性上是先在于个人和家庭的。但自基督教文化产生以后,共同体范畴的内涵逐渐变得狭隘,只有具有主体性的人才能在共同体中占有一定位置。至此,共同体范畴变成了一种理性的共同体,人类之外的其它自然存在物被排斥在这一范畴之外。但伴随着生态科学的成长,对共同体的理解和描述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生态学知识为共同体概念提供了真正的科学描述,使人们摆脱了自然的主人和征服者的角色,逐渐明白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人类是依赖于这个共同体而存在的,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对此,纳什指出:“通过创造一种具有生物共同体意蕴的新概念,生态科学也为道德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2(]P8) 而共同体生态化及其本身能否具有道德意义既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生态伦理观确立的关键之一。因为首先它直接关涉到生态伦理学对道德关怀对象范围的拓展问题;其次它涉及到人、社会以及自然如何协调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问题。为此,利奥波德借助于生态学的范式作用,强调从生态性的整体层面来理解这一范畴。因为在前生态学时期,共同体观念是与古代神秘主义以及神学中的有机体主义内在关联,这使其缺少了科学基础。而自生态学产生以后,它就为共同体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生物学基础,使人们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寻求其存在的基础。生态学“为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使之包括大自然提供了许多实践性的理由,还为其它物种、甚至作为整体的环境的内在权利提供了一个论据”。[2](P20)要确立生态共同体的道德价值,关键是如何解决生态系统——生态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单从生态学含义上讲,完全可以把生态系统直接等同于生态共同体。 关于生态系统能否是道德共同体的问题,生态伦理学主要是依托生态学范式,并着眼于系统整体的利益或价值来强调生态共同体是道德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大地伦理学中,利奥波德对生态共同体概念的界定有如此表述:“土地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应该被热爱和被尊敬,则是伦理学观念的延伸”。[1(]P6)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其自然价值论伦理学中继承和发扬了利奥波德的生态共同体是道德共同体的思想,并提出要使生态共同体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共同体,需要证明这一共同体本身就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们借助生态学的范式作用,采用多层次的、系统性的整体视角诠释生态共同体。从方法论的角度,单一的个体视角并不能为生态共同体(生态系统)成为道德共同体提供充分的理论判据。尽管生态系统中有机个体内部以及有机体之间的生存与斗争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这“不是按照大自然自身所是来判断大自然”,是一种范畴的误置。这就要求我们在论证生态系统的道德性时,立足其自身固有的特质,转换视角确立一种生态——整体的观念。#p#分页标题#e# 在生态学意义上,生态系统和生存于其中的有机个体之间是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生命之网。并且生态系统通过有机个体表征出来的合作与斗争并不是无限扩张的,这些行为要受到系统本身的约束和限制,例如进化生态学的优化理论描述了生态系统对于物种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因为,系统自身的过程性促使有机体紧密相连、相互合作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生态系统的外部过程与内部过程共同支持着有机体的生存发展,所以我们要赋予生态系统与有机过程一样的尊重。有机体之所以能够被纳入到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就在于它具有自我的内在目的性。这种有机目的性是与它自身的生理特征密切相关,例如,中枢神经系统、基因组等。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正是依据有机体自身固有的目的性赋予其道德地位。 所以就生态系统自身固有的特质而言,它看似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且不拥有和有机个体一样的目的性,但是它通过强调系统的过程性以及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却使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有机整体性。这种“松散性”,我们不难发现,在其本质上,生态系统或生态共同体就是一个遵循着“共同体式的整体主义”,即一种在程度上弱于有机整体主义的形式,并且以自身为范式的、能自我修复的、开放的、有序的生命系统。它的这种维持系统完整、平衡、和谐和美丽的松散性、秩序性和创造性在利奥波德的视域里就是其获得道德意义的依据。这样就从系统整体的视角给生态共同体搭建了一条从描述性的范畴转向一种规范性的概念的逻辑通道。简单讲,以大地伦理学为代表的生态伦理学正是基于生态学的范式作用扩展了共同体的内在涵义,由此达到了对存在于人际关系范围内的共同体范畴的生态化,赋予了自然相应的伦理地位,进而为强调人——社会——自然三者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提供了逻辑基点。 三、大地伦理学的生态伦理观:生态文明的伦理之基 在大地伦理学中,利奥波德力图通过伦理观念的生态化,以便改变以往以人为中心的自然观和价值观,其目的是建构一种有别于传统伦理观念的生态伦理观。因为近代以来,西方传统哲学由于受实体论理念的引导,形成了过于重视和信赖理性的观念,这就为近代机械——还原论自然观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因子和逻辑前提。近代的自然观把自然视为一架听命于人类意志的冰冷机器,它既无生命又无内在理智,更无推动自身运动的内在秩序。其造成的直接后果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观念上,人类开始轻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自命自己为宇宙的主宰;其次,在实践上,丧失了灵性的自然变成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发展而必须进行征服的对象。正是由于自然观念的根本转向,所以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忽略了给环境带来的破坏,而环境危机也由此变成人类的梦魇。那么,人类究竟以何种姿态面对在自然呢?利奥波德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具有生态意识,学会向创生万物的大自然学习;其次,要在此基础上摒弃以往以人为主体的伦理观念,建构一种给予所有非人自然存在道德关怀的生态伦理观念。就其社会功能而言,这一新的伦理观能够恰当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进而使人类社会逐渐远离黑色文明走向绿色的生态文明。因为从人类文明发展态势来讲,建设生态文明是顺应时代的需求。而无论何种文明不可或缺的都是人,所以生态文明如何得以发展以及怎样发展都要取决于当下在场的人类。所以就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而言,首先要树立生态理念及生态整体思维模式;其次从规范角度看,需要确立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伦理原则、道德标准来规范人类的社会行为,而大地伦理学的生态伦理观恰恰为此提供了适当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基础。